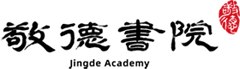徐勇:中国传统师道——德行美好 学识丰博
作者:徐勇(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敬德书院学术委员)
无论是在历史文献中还是在现代语境下,“师道”都是一个有着多重含义的概念,但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为师之道,二是指教师的地位、作用以及尊师的风尚。在这里,我仅就前一个内容即为师之道来谈“师道”,探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合格的教师应该具有怎样的特质,或者说,传统文化对于一位教师有着怎样的期待和要求。中国传统文化高度尊重教师、礼敬教师,与这种尊崇相适应,全社会普遍对教师有着极高的期待,对教师有着很高的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希望和要求一个教师德行美好、学识丰博、尽心敬业、善教有方。 德行美好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人为出发点和根本来观察和思考问题。北京大学的楼宇烈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一书中,把这种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的文化,描述为“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并称之为中国文化的人本思想和人文精神。在排除了人的命运为天神所主宰、为外物所役使之后,决定人的命运的根本因素,就是自己的德行。这也就是周人在总结商亡周兴的历史教训时所说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就是明朝袁黄在教给自己儿子的《立命之学》中所说的“命由我作,福自己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修身养性、积善行德和人的命运之间有着内在的、直接的关系: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只要持续地改过迁善、立善行德,就能够趋吉避凶,有余庆而无余殃,从而把握自己的命运。《左传》说:“德,国家之基也。”一个人是如此,一个王朝、一个政权也是这样。 基于这样的理念,传统文化就由以人为本,自然地迁转到了以“德”为本。《左传》说“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老子》说“重积德,则无不克”;《论语》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礼记》说“富润屋,德润身”“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新语》说“积德之家,必无灾殃”;《论衡》说“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汉书》说“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后汉书》说“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三国志》说“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士有百行,以德为首”;《资治通鉴》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等等,众口一词,都说明了“德”的重要。以“德”为本,就要敬德、崇德、黾勉行德、积善累德。周人甚至提出要“疾敬德”,也就是要调动自己的全部潜能、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急切紧迫地向德趋赴,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朝德迈进,快速提升自己的德性和德行。教育教学、读书学习,就更是要以立德树人为目标。对于学生而言,读书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变化气质,涵养性情,学会做人之道,明白事理,懂得如何为人处事。 另一方面,教师的职业特点,也决定了教师德性的重要。《玉篇》有言道:“师,范也,教人以道者之称也。”西汉学者扬雄在《法言·学行》中指出:“师者,人之模范也。”明太祖朱元璋也说:“盖师所以模范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才力,各俾造就。”形端才能影正。铸模造范,必须端正规整,不差毫厘,否则,由此模子范式中生产的产品,就会无一例外地存在瑕疵。正如石成金在《传家宝初集·卷之二·师范第十》中所说:“为师者,弟子之所效法。其师方正严毅,则子弟必多谨饬;其师轻扬佻达,则子弟必多狂诞。是以文人才士,虽不必过于迂腐,但俨然为人师范,举动间亦须稍自检束,令子弟有所敬惮。”一个合格的老师,必须是学生行事的榜样,视听言动的模范。教师只有具有了良好的品格和风范,才有可能把学生塑造成“圣贤的坯璞”。 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意识到了教师的榜样作用,都强调身教重于言教。教师的以身作则、以己示范,是比给学生一大堆规则、反复进行道德说教更为有效的教育。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教育环境,通常都规模较小,人数较少,师生朝夕相处,相互熟识,共同建立起了人文教育所必需的亲密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教师的品质、人格、习惯和处世态度,就会时刻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熏陶。正如宋朝人俞文豹在《吹剑录》中所说的那样:“所谓师弟子者,皆相与而终身焉。难疑答问之外,则熏陶其气质,矫揉其性情,辅成其材品。如良工之揉曲木,巧冶之铸顽金,蜾蠃之咒螟蛉。使物物皆曲成,人人皆类我,而后为无歉。吾夫子之陶铸七十子,盖如是也。” 由于教师不仅肩负“授业解惑”的传习使命,而且怀负“时而化之,德而成之,材而达之”的教化责任,所以,中国古代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也无论是学塾还是书院,都非常注重教师的德性和德行。在选择各级教师时,把这点放在首要的位置。清代的李淦叮咛家人:“既谓之师,必其范足以为楷模而后可。故当择其文行兼优者为上,文优而大德不逾闲者次之。若品行有亏之人,虽文才出众,教法超群,不敢请也。”即便学识丰博、高明善化之人,如果德性有瑕疵,德行不检点,那人们也不敢请,最终不会请。很多家族在选择塾师时,都有这样的要求。 为了确保教师的品质,古人设置了很多的门槛,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具体条件。魏校在督学广东时规定:“教读不许罢闲吏员及吏员出身之官,或生员因行止有亏黜退者,丁忧者及有文无行、教唆险恶之徒。下至道士、师巫、邪术人等,宜先自退避。”明确规定了罢闲吏员、黜退生员、有文无行之徒、道士邪术之人等不能担任教师。他同时还规定,一旦发现有人“隐情冒教”,一定要查究革除。明末清初的冯班,强调延师时要远离市井浮薄之人,“得淳厚有家风者为上,其次则自好喜读书者”。《粤东议设启蒙义塾规则》高度注重塾师的选择,认为只有“人品端方,学问通彻,不嗜烟赌,而又不作辍、不惮烦、勤于讲习者,方足以当此任。”有一些地方官和家族甚至规定,塾师不能选择轻佻、放浪、浮躁的年轻人,而必须是40岁以上的、齿德俱尊的老成之人;不能选择品行难以访问、为人不易了解的外地人,而有必要选择非亲即邻、相处已久,道德品行、已有公论的本地人。 学识丰博 教师的职责不止于“授业解惑”,但也包括了“授业解惑”。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没有好的品行不行,但只有好的品行而没有一定的学识更不行。可以想象得到,一个教师如果没有起码的学识,教学活动根本就无法开展。所以,古人在强调一个教师要“行谊谨厚”时,也要“文义通晓”;在突出“立品端正”“品行端方”“敦品励行”的同时,也指出“才华擅长”“经书熟习”“学问通彻”的绝对必要;在说明教师必须“以身率人,正心术,修孝弟,重廉耻,崇礼节,整威仪,以立教人之本”的同时,也强调要“守教法,正学业,分句读,明训解,考功课,以尽教人之事”。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经明行修、品端学粹、品学并称、文行俱美,或者说是行为世范、学为人师。 在论及师道时,古人时常感叹师道的逐渐式微。在清中期的陆以湉看来,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夏商周三代,最重视的是道德;而两汉时期,人们重视的是经术;唐宋时期,重视的是辞章;而明清时期,更降而为举业。“有志世教”的他“思所以救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经术、辞章和举业就百无是处,无益可废。实际上,在他的著述《冷庐杂识》中,就有诸多夸赞教师指画有方、让学生一举高中的事例。他不过是在感慨师道的日益狭隘,越来越偏枯,越来越不丰盈,走上了“自广衢趋于狭径,弃磊落而注虫鱼”的道路。问题出在本末倒置,轻重失次,而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弃经术、辞章和举业。 明朝学者冯时可在《雨航杂录》中,打过这样的一个比喻:“节义”好比读书人的“门墙”,“德行”好比读书人的“栋宇”,“心地”好比读书人的“基址”;而“文章”好比读书人的“冠冕”,“学问”好比读书人的“器具”,“才术”好比读书人的“僮隶”。诚然,基址不坚,栋宇不固,门墙不稳,难有大厦的巍然挺立,但没有冠冕、器具乃至僮隶的装饰,也不成华屋,难以称之为美轮美奂。进而言之,没有一定的知识和学养做基础,就难保德行不偏离正道,不流于表浅。所谓的“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贱;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说的正是这个意思。离开了学的滋养,任何德性都会枯涩。只有具备一定的学识,才有可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德性和德行,把问题看得深刻,对道理理解得透彻,才能有效地克服行为的盲目性和偶然性。所以,学识既以德行为依归,又是德性的保证。 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拥有丰博的学识本身就是一种美德,所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作为教师“祖师爷”的孔子,他好学的精神、丰博的学识和他以身作则、以己示范,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的师德,共同构筑了“万世师表”的风范。他号召人们“博学于文”,认为只有和学问广博、见识丰富的人做朋友才有意义。他鄙薄饱食终日的懒惰,蔑视无所用心的自满,谦称有德性比他好的人,自信没有比他更好学的人。他忘情于学,以至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甚至“不知老之将至”。他学而不厌,老而弥笃,一部《周易》,就被他读得“韦编三绝”。他不以“生而知之”自居,不以“不学自知,不问自晓”自诩,本着学无常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态度,一以贯之地“每事问”,随时随地不耻下问,以开放的心态,增益自己的知识,扩充自己的眼界。正是因为这样以学为志业,好学乐学,他不仅通晓并有能力整理和写作《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文化典籍,而且多识鸟兽草木之名。面对博学多通的孔子,人们一方面由衷地感佩,称颂“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另一方面把他当作一部百科全书般地请益问疑。汉代的扬雄在《法言》中直接说:“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本文来源于海淀教科研丛书《温馨的师德》,现代教育出版社)
未 完 待 续 专 栏 学术论横 责编 | 水芙蓉 美编 | 水芙蓉
供稿: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