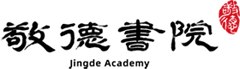曾海龙 | 十力学派与儒学的现代转化(下)

三、儒学现代转化中的十力学派
现代新儒学依然是个正在发展的课题,作为现代新儒学主力的十力学派,对现代儒学的发展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当下也依然受到学界的重视。就十力学派之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意义特别是儒学的现代转化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十力学派是以哲学化的“心性之学”创造儒学存续的新形态
现代儒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以哲学学科的框架来定位、阐发与研究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古典思想。晚清在废除科举制的同时,逐渐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现代学科体制。在现代学科体制中,并没有设置研究儒学或儒家经典的学科门类。无论是类似于汉唐或有清一代的经学,还是类似宋明理学那样的学术形态,都在现代学科体制中无处容身。康有为式的儒学及其命运,既表明儒家思想必须实现创造性转化,也意味着传统的学术路径已经走向了终结。在康有为之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无论是就思想形态而言,还是就学术形态而言,儒学都必须构建新的论述主题与论述范式,才有可能适应现代学术体制,以图在现代社会生存。如果说康有为终结了传统儒家的思想形态并开创了新的形态——成功与否暂且不论,那么胡适就彻底终结了传统尤其是传统儒家的学术形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可谓是斩向传统学术方法与学术形态的“最后一刀”。在这之后,无论是传统的思想资源,还是阐发传统思想的学术方法,都必须接受现代学科体制规范的检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开创了儒学乃至传统学术的一种现代路向。
《新唯识论》被誉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哲学著作”,无疑有将其视为中国现代学术成果的意味。这一评价既意味着儒学作为一门学问已经存在于现代学科体制之中,也意味着现在的儒学已经不再如传统儒学那样,能全面主导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儒学可以作为哲学学科研究的内容与对象,容身于现代的学术体制中。而作为一门学科内容的儒学也表明其不再追求对政治社会的全面主导权。20世纪下半叶,熊十力被动地沉寂于书斋,他的弟子则多艰难栖身于港台和海外的大学或科研院所,以哲学话语与学术范式阐释儒学的精神价值,无疑是儒学在现代社会真实的生存样态。十力学派所代表的儒学的现代形态,也意味着儒学在脱离政教制度的场域之后,在学术领域获得了新生。
(二)十力学派试图在学理构建的同时以一脉心传的方式延续道统
在现代新儒家群体中,十力学派对道统的坚守别具一格。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及其弟子的著述,都呈现出这个群体清晰而强烈的儒家道统意识,这意味着十力学派有着基于文明传统的特定精神追求、生命样态与价值传承。新唯识论所体现的儒家道统意识深刻影响并左右了学界对现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家的认定标准,熊十力也因此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山。实际上,相比于其他早期现代新儒家,无论是就才情还是就学识而言,熊十力都不算出类拔萃。但《新唯识论》无论是作为哲学论著所具有的现代学术特征,还是其呈现的儒家道统意识,都是早期现代新儒学的著述中最为明确的。
梁漱溟比熊十力早出,其儒学、佛学功底及其对西方思想的了解,都不在熊十力之下,甚至超过熊十力。在“五四”时期,梁漱溟率先扛起儒家的大旗,在学界和政界都有较大的影响。这些都是熊十力所不及的。熊十力的学术道路得到梁漱溟的诸多帮助,二人可谓学术上的诤友。然而,梁氏虽天资聪慧,出身书香门第,各方面条件都比熊十力要好,但在哲学上的创见实则没有熊十力丰富,且其终极关怀是否为儒家还是需要商议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梁漱溟的关注点及其影响主要不在哲学理论与性理之学方面,而是在文化上,他思想成熟之后的主要精力更多地放在了政教实践与乡村建设上。总体而言,梁漱溟虽然是开风气的人物,但在构建哲学体系方面,相比熊十力而言还是要逊色不少。陈荣捷就指出:“梁(漱溟)给予儒家仁的概念以力动直觉的新释,但他没有造一个自己的哲学系统。熊则做了这一件工作。此外,他比任何其他当代中国哲学家影响了更多年轻的中国哲学者。”[13]同时代的马一浮,学识与修养均不在熊十力之下。但马一浮处于出世入世之间,不喜著述,虽学识渊博却欠缺精进,因而创造力与影响力较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要弱。冯友兰所走的则是新实在论路向,其思想自成一家,其著《中国哲学史》可谓以现代学术方法研究古典思想的开创性著作,在学界影响颇大。但冯氏对于儒家思想尤其是孟子、象山到阳明一派学脉的了解,以及继承儒家道统的意识等方面,终究与熊十力等人不在一个层面。贺麟曾留学西方,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有相应的了解,但他受益于黑格尔又受困于黑格尔,虽一度倾心于儒家思想并写出若干著述,但“客观精神”与“逻辑学”的基底又让他始终与儒家的“仁”有一定距离,因而其儒家特征不如熊十力那样直接与犀利。张君劢的主要贡献在文化论述与政教制度的构建方面,与梁漱溟一样在哲学体系的构建上有所欠缺。此外,钱穆的主要学术贡献在史学方面,虽有着强烈的文明论意识,但他是否为现代新儒家则还存在争议。[14]总体而言,在早期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体系构建与著述中,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哲学及其代表作《新唯识论》最具原创性,既体现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论特质,也表现出强烈的道统意识。
(三)十力学派试图以对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来接合“现代性”
十力学派在有着强烈的道统意识的同时,也有着鲜明的“现代性”意识,呈现出融汇古今中西的开放特质,对儒学的现代转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现代新儒学与宋明儒学(新儒学)的根本差异,就在于现代新儒学有着鲜明的“现代性”意识。这种意识,集中体现在现代新儒家们大多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精神,以古典儒家的思想资源去支持并论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张。“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乃至“里勃耳特”(liberty)等基本观念,逐渐深入现代新儒家的精神世界,进而成为他们的基本主张与政教目标。这一点对于十力学派来说也不例外。熊十力早年对辛亥革命后世道人心不满,大约也有传统不能尽除之憾。直至《新唯识论》面世时,他都没有对康有为等人的“保守”抱持多少敬畏与好感。他自始至终对“自由”的呼唤,无疑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价值主张遥相呼应。他的弟子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乃至第三代港台新儒家刘述先、杜维明、李明辉等,无疑都认同“五四”的基本价值。徐复观创办的《民主评论》,表面是在与《自由中国》相抗衡,事实上却是在呼应自由派的主张,二者的分歧只是在于如何看待传统。陈明曾评价说:“李泽厚是五四下的蛋。”[15]实际上,现代新儒学特别是港台儒学也是“五四下的蛋”。他们虽钟情于传统,却又是以古典的思想资源(主要是宋明理学)来论证“五四”所主张的“现代性”价值。也就是说,他们在“打倒孔家店”的运动中,以“孔家店”的遗产来支持与论证这场运动的合理性。如果说康有为是以今文经学的资源和方式来谋求“以夷变夏”,那么十力学派就是以宋明理学的思想资源与现代学术方法来论证“以夷变夏”。这种方式当然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对确立儒学乃至古典思想的现代形态具有典范意义。
(四)十力学派深刻影响甚至左右了现代儒学的发展样态
十力学派至今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并将继续影响儒学的现代形态,进而继续影响中国化的“现代性”构建与现代化道路。熊十力的弟子们继承了他的思想方向,延续了他开创的学脉,并将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奇观。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儒学研究者,只有港台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在学界掀起了比较大的波澜。但钱穆走的是史学的路向,从其对《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态度也可看出其对“心性之学”的态度,其学生余英时则完全否认钱穆为新儒家。因而,唯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继承了“心性之学”的理路并将之发扬光大。而此三人都为熊十力的学生,虽然徐复观对熊十力的思想理路有所批评,但以“心性之学”来概括三人的学问则应是大体不差的。无论在生命情怀还是在学问取向上,此三人都与熊十力有内在的一致性。在1949年以后的几乎半个世纪里,大陆的儒学没落,港台则由熊十力的门人领军,使儒学特别是熊十力的思想与学脉在异乡开花结果,几成异数。20世纪70年代牟宗三领军的“鹅湖系”,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中,培养出一批儒学研究者与儒家精神的继承者,对中国港台及海外儒学与20世纪80年代后的大陆儒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在港台对新儒学的开创而产生的盛况,阳明后学以降,恐怕未有可与之媲美者。这几乎都是继承熊十力学脉的港台学人所开创的,与熊十力的思想尤其是《新唯识论》有着内在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当代儒学的主要人物或儒学研究者,相当一部分与熊十力、牟宗三等有莫大的关系,熊十力开创的“现代心性之学”依然是儒学的主流之一。
大哲牟宗三逝世后,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等人在港台和海外所开创的儒学研究局面暂时告一段落,但继起的与当下仍活跃的儒家学者或儒学研究多与此三人有关系。杜维明是徐复观的学生,同时也深受牟宗三的影响。刘述先是方东美的学生,也可说师承牟宗三,并受到熊十力和徐复观的思想影响。“鹅湖系”中的蔡仁厚、杨祖汉、李明辉、林安梧等,都是以牟宗三为师。虽然在思想资源、理论入路、方法论以及儒学的作用上与其前辈不大相同,理论的具体关注点也不大一样,甚至其内部也存有学理争议。相比上一代而言,他们在学界的主导性不再那么明显。然而他们人数众多,并致力于将学理传到大陆学界和海外,对扩大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哲学思想的影响起了巨大的作用。以“鹅湖系”为主的“鹅湖学派”“牟宗三学派”[16]等都可以看作是十力学派的延续。他们致力于发扬光大儒家的思想,对“心性之学”内在理路的肯定,也基本上是一致的。总体而言,这些学人所论可视为熊十力所开创的“现代心性之学”的展开。另外,他们在生命情怀、终极信仰上也大多服膺于熊十力和牟宗三所代表的心学路向。
在西风凛冽的时代背景下,十力学派试图以儒学的精神资源来接合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进而思考现代中国的构建。这种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建立联系的努力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思想面貌。熊十力晚年的政教主张就与其早年的致思颇不一致,以至于和他的弟子在学术和政治上分道扬镳。但在结合甚至构建“现代性”与构建现代中国这个目标上,却未曾有动摇。熊十力对现代儒学已经产生的影响,也主要因为其早年的《新唯识论》。而十力学派之所以为人所瞩目,不仅是熊十力本人的《新唯识论》以及其弟子唐君毅、牟宗三等人改变了儒学传统的思想范式,确立了儒学研究的哲学形态,也因为在儒学的现代转换中,十力学派是无可争议的中坚力量。这一点,我们从现代新儒学的界定与分期以及学界对现代新儒家的认定就可以看出。十力学派的努力与创获,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也将历久弥新。
四、儒学现代转化中的十力学派及其挑战
自19世纪中叶开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中西文明交涉之后,至20世纪初,实现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精英们的基本共识。但何为现代化,需要实现何种程度的现代化,以及如何现代化,才是中国人观念与实践中最具争议的根本性议题。作为现代化负面资产的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在经历了刀刀致命的轮番刺割之后,催生出了为儒学辩护的现代新儒学。然而吊诡的是,现代新儒家们的主要议题,却是以传统思想资源去论证并支持给传统“最后一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主张的价值观念。[17]作为现代新儒学主流的十力学派,自然也莫之能外。
熊十力以佛教唯识学的理论框架与方法阐发的儒家性理之学,在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之后,开创现代新儒学之荦荦大端,更将儒家思想以哲学体系化的范式呈之于世。之后经牟宗三等十字打开,以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重构儒家心性义理,并构建“道德的形上学”;唐君毅则以黑格尔之理性精神接纳融会儒家的理想人格,以成就道德的自我。熊、牟、唐这种通融中西的学理形态,深刻影响甚至左右了现代儒学的发展路径,时至今日以哲学化方式阐释儒学乃至传统思想仍然是学术主流。徐复观等人也深受熊十力生命气质的影响,在吸纳现代学术方法的同时,也继承熊十力的道统意识。这些熊氏弟子在港台和海外多存有“孤魂”的心态,以研究儒学纾解悠悠“乡愁”,并以自身的道德人格和学理构建,吸引了一大批学人从事儒学研究。他们创办或参与的鹅湖书院、新亚书院,成为港台儒学研究的重镇,培养了一批致力于研究传承发扬儒家传统并沟通中西的学人。总体而言,这些港台儒家和儒学研究者都继承了熊十力早年的道统意识与思想方向。[18]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以坚守儒家的价值为人生追求,以现代学术的方式来从事儒学研究。同时,他们又与现代新儒学的其他学者一样,多栖身于现代大学或学术研究机构之中。
就晚清到民国的历史背景与学术脉络而言,熊十力的代表作《新唯识论》及新唯识论体系,既代表了一种现代背景下的学术思想创造,也表明传统在遭遇“现代性”时,必须转化其存在方式才可能获得恰当的安顿。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给中国传统最后的致命一击之时(1905年废科举、1912年清廷灭亡,对儒家尤其是建制儒学或制度儒学而言都是致命性的打击),传统就不得不开始其自身的现代转化。十力学派正是传统儒学向现代转化的标志之一。而儒学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或现代化,既是中国古典文明传统存续的象征,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性”构建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现代新儒学的出现,乃是儒学的“现代性”构建的基本内容及其存在方式。
在传统儒家的理论体系中,“内圣开出外王”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核心的架构。在这样的架构中,“内圣”作为儒家的道德人格理想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作为政教秩序的“外王”则是道德人格理想的外在延伸。无论是“得君行道”上行路径还是“觉民行道”的下行路径,都基于对这种架构的认定。也就是说,无论是主张君权还是主张民本,都需要强调德性之于政教的基础性与优先性。现代新儒家对“五四”的批评主要是就这方面而言,而他们对“五四”精神价值的支持并构建自身的现代性论述,也是基于此种传统。而发端于西方的现代秩序,则基于道德与政治的分离。亦即是说,现代西方文明不再以德性为政治的前提,不再致力于以政教制度的构建来成就人的德性。十力学派所采取的方案,就是将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民主、自由乃至科学纳入“内圣开出外王”这一理论架构中,亦即视现代政治也可为儒家道德理想所涵摄,因而有所谓“内圣”开出“新外王”。在此意义上,十力学派才被称为“现代心性之学”。
无论是“现代新儒家”之“新”,还是“新外王”之“新”,都在于肯定民主、自由、科学等各种发端于西方文明的“现代性”要素,进而以构建现代性或现代政制为最终目标。也就是,现代新儒家之“新外王”,就在于肯定“现代性”并以此为理论构建目的。但无论是古典儒家的“外王”还是现代新儒家的“新外王”,都是以成就理想道德人格的“内圣”为基础(有些现代新儒家提出的“新内圣”亦不超出“内圣”范畴),来构建政教秩序。十力学派大体是将民主、科学等各种现代性要素纳入“内圣开出外王”的传统架构中,以“新外王”取代或补充“外王”。然而,这种主张起码会遭遇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来自建制儒学或制度儒学的挑战。现代新儒学特别是十力学派以“心性”为基础的道统、学统与政统的构建,是在康有为等人以经学资源构建现代中国政教方案失败后,儒家通过审思自身传统来接合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的结果。但如果以康有为的视角与问题意识来看,十力学派认为儒学是心性之学并将复兴的重心放在“心性”方面,无疑是自缚手脚乃至自我戕害。近年来“新康有为主义”的兴起及其对港台新儒家的批评,无疑是十力学派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与现代新儒家尤其是港台新儒家主张心性儒学或哲学为儒家之主要方面不同,“新康有为主义”主张政治儒学或经学,强调中西文明传统之异,主张以本土的资源完成现代中国的构建。“十力学派”则试图论证儒家思想与西方民主、科学之相容性,希望在中西之间求同。[19]就理论层面而言,“十力学派”可以对“新康有为主义”等建制儒学或制度儒学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应,然而在实践层面则很难解决这些问题。
二是来自现代新儒学内部的挑战。狭义的现代新儒学(十力学派)与广义的现代新儒学的根本差异,就在于是否以“心性”架构与哲学构建的方式去接合西方的现代观念。因此,现代新儒学内部对十力学派以“心性”接合“现代性”以构建现代方案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余英时等人就与十力学派在“内圣”开出“外王”的看法上有着重大的歧见。在余英时看来,《大学》的修、齐、治、平必须从现代的观点来重新解释。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将“内圣”与“外王”分开来处理。他说:“现代儒学必须放弃全面安排人生秩序的想法,才能真正开始它的现代使命。为什么呢?关键即在于儒学已不可能重新建制化,而全面安排秩序则非建制化不为功。”[20]这虽与建制儒学或制度儒学的立场不同,却秉持了相同的逻辑。也就是说,完全“心性”化的儒学既不可能再全面安排人生秩序,更不可能构建政教制度。
三是来自自由主义者的批评与挑战。殷海光、张佛泉等自由主义者与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十力学派第二代,曾就“政治自由与民主是否需要道德基础”这个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涉及十力学派所关涉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形而上学与政治或心性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论战的双方观点鲜明。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与“民主”并不需要一个形而上学作为基础,政治自由也不需要以意志自由(心性)为前提,让心性、形而上学问题纳入政治理论与政教实践中,反而会模糊道德(心性)与政治之间的界线,并可能导致极权主义。对于现代新儒家来说,民主政治是道德价值之体现,坚持政治自由必须以意志自由为基础,也就是说,现代民主政治必然需要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心性论基础。这场争论虽围绕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家的主张展开,却对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申论,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其意义。殷海光将“以道德作民主政治的基础”者称为“传统主义者”,并认为他们持一种“泛道德主义的”(panmoralistic)立场,这种立场又系置于与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panlogicism)及其相近的“形上学基础”之上,显然是针对牟宗三等港台的十力学派。[21]十力学派力图以“心性”架构在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之间建立某种连接,既以传承儒家古典精神为使命,亦以构建某种现代方案为目标。而自由主义者却认为,二者之间产生断裂,才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条件。
以“心性”为核心概念与基础来构建“现代性”,反映了十力学派乃至现代儒学的两难与尴尬。一方面,建制儒学与制度儒学构建的现代中国方案失败之后,儒家不得不以“心性”架构来接合“现代性”,以表明建制儒学与制度儒学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儒学具有反现代的特质,进而为自身存续的合法性进行辩护,而这种辩护的理据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自身的传统;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在于道德与政治的分离,而以“心性”之学为自身存续的合法性辩护的儒学,必然会遭遇诸如自由主义等外来观念的挑战。
干春松曾评价《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所呈现的十力学派的立场与心态。他说:“《宣言》明显带有一种‘东方主义’的立场来批评东方主义。这种批评更接近于文化的批评,实质上构成了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曲通’。所以《宣言》的最后更多接近于对西方的‘规劝’而非儒家立场的自我宣示。”[22]
也就是说,《宣言》既是对西方的“规劝”,也是对“现代心性之学”招致现代儒学内部批评的反驳与辩护。在这个意义上,十力学派同时需要应对内部与外部的挑战。在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之后,杜维明、刘述先、李明辉等十力学派后学,不再如他们的前辈们那样有道统坚守与政统的企图,而是将主要精力转向了学理的建立,表明“心性之学”要想全面落实关于人生秩序的安排,已经不可能了。事实上,现代社会的多元架构已经难以避免,儒学由原先整全性的社会价值体系转变为学科化的知识体系,也正在成为现实。既然儒学难以有存身之所,不得已而成为“游魂”,那么如何使其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在中国人的心里存续,成为我们安身立命的价值根柢,才应是儒学在现代所追求的目标。几代十力学派成员的问题意识和学理传承与演绎,也在印证着这个课题。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典诠释学基本文献整理与基本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055)、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儒学的现代性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20FZXB068)阶段性成果。
[1] 1986年,方克立、李锦全等主持了为期十年的“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项目。方克立说:“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方克立:《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几个问题》,《方克立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18页)按照这个标准,则确定了一个现代新儒家的名单: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后来又加上了马一浮,并扩展到杜维明、余英时、刘述先和成中英。
[2] 十力学派这个概念,是笔者在博士论文《本体的困惑——熊十力哲学思想研究》(复旦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来的,近年来这一概念开始为学界所认同并使用。杨泽波著《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一卷·坎陷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页)与《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2—7页)都使用了这一概念,并阐明从熊十力到牟宗三一系的思想特质。杨泽波近年对十力学派的思想的发展,尤其是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进行了一系列的阐发(具体参见:1.《从“十力学派”的视角看牟宗三儒学思想的贡献》,《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2期;2.《“十力学派”遗留的一个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兼论儒家生生伦理学为什么以“生生”为切入点》,《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3.《“一体”的传承——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一》,《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4.《“道德践行之呈现”的传承——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二》,《齐鲁学科》2022年第3期;5.《“道德存有之呈现”的传承——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三》,《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1期;6.《“一体两现”:熊十力思想核心之分疏》,《江汉论坛》2023年第3期),并在《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持了“关注‘十力学派’”的专题(《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另外,近年来也有以十力学派为研究对象而撰写的学位论文(比如:西北大学杨超宇于2018年撰写的硕士毕业论文《“十力学派”体用论建构历程及其影响研究》)。还有学者使用了与本文所论的十力学派内涵一致的概念,比如,刘又铭《一个当代的、大众的儒学——当代新荀学论纲》,关注熊十力到牟宗三一脉的发展,但将其称为“熊牟学派”(参见刘又铭:《一个当代的、大众的儒学——当代新荀学论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页)。
[3] 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季羡林编:《胡适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6页。
[4] 参见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沈志佳编:《现代学人与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5] 参见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6] 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和张君劢签署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后简称《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总体上代表了十力学派第二代及其部分后学的关切点。他们认为,儒家精神或“道统”主要系于“心性”传统,而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存在于道统之中,道统是中国文化之根。
[7] 干春松认为,钱穆与狭义新儒家的差异,从学术上看,主要是对儒学的形态和核心精神之认识的差异。与十力学派或狭义新儒家所主张的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儒学史认识不同,钱穆将儒学史分为六期,强调儒家思想是包含文学、历史、经学和政治在内的复杂的文化系统,并非只有“哲学”这一面向。因此,钱穆并不认同宋儒所提出的“道统”思想,他认为整个文化大传统即道统,而非一脉心传的抽象道统(参见干春松:《儒学的近代转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99页)。
[8] 三代四群是刘述先综合各方的意见而提出的,具体如下:第一代第一群: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第一代第二群: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第二代第三群: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第四群: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参见刘述先:《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9] 参见刘述先:《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第170—171页。
[10] 参见曾海龙:《大同是理想还是现实的运动?——基于熊十力与康有为的立场》,《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11] 马一浮:《序》,萧萐父主编:《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熊十力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12] 参见杨泽波:《“一体两现”:熊十力思想核心之分疏》,《江汉论坛》2023年第3期。
[13] Chan Wing-tist, trans. and comp.,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76.文中引文由刘述先译出,参见刘述先:《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第178页。
[14] 参见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沈志佳编:《现代学人与学术》,第21页。
[15] 参见陈明:《启蒙的意义与局限——思想史视域里的李泽厚》,《人文》编辑部编:《人文》(第7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
[16] 参见程志华:《台湾“鹅湖学派”的理论渊源、代表人物及义理走向》,《东岳论丛》2013年第6期。
[17] 余英时认为,晚清儒家既受王阳明、黄宗羲等传统儒家君权观的影响,也受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启发,因而突破了儒家传统的限制,发现了解决君权问题的具体办法。但无论是今文学派主张孔子立教之初便“废君统,倡民主”(谭嗣同《仁学》第三十),还是古文学派强调“君主之任位有定年,与晰种共和政体同”(刘师培《古政原论》),他们仍然是站在儒学系统的内部来理解民主的意义。与其说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毋宁说他们扩大了儒学的系统,赋予了儒学以现代的意义。可谓“旧瓶新酒”(参见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76—177页)。
[18] 熊十力晚年的政教思想发生了重要乃至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标志就在于晚年的熊十力汲汲于“大同”,而绝不言自由,甚少提及民主。在这个意义上,熊十力晚年已经偏离了早期现代新儒学的立场。当然,此一现象几乎体现在所有新中国建立后留在大陆的传统学者身上。另外,熊十力晚年的主要精力在经学方面,这与港台儒家以心性之学接纳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而与康有为的方式更为接近。熊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除了徐复观对《读经示要》评价颇高之外,其余多视《新唯识论》为熊十力的代表作,而熊十力晚年的著述,更是受到港台弟子们的轻视甚至嘲讽,更遑论对其进行继承与研究。
[19] 参见曾海龙:《从现代新儒家到大陆新儒家——以“新康有为主义”为中心的考察》,《国际儒学论丛》2017年第2期。
[20]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第181页。
[21] 参见曾海龙:《儒学现代演绎中的欧陆路径与英美路径之交锋与交融》,《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22] 干春松:《儒学的近代转型》,第221页。
来源:孔学堂杂志社公众号
供稿: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