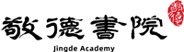徐洪兴,陈华波:德性实践与德性之知——论二程经学诠释的转向
作者简介丨徐洪兴,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上海哲学学会中国哲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兴趣和方向在中国哲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
陈华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传统经学诠释有训诂、义理之分,北宋二程的经学转向进一步揭示出经学诠释中的“德性”内涵。二程经学思想不啻是义理之学,更是德性之学,它包含了德性实践和德性之知两个维度。二程将诠释重点从作者和文本转向读者,将治经问学的目的从知性理解转向德性实践,这就脱离了形式上的训诂之学。同时,又指出以德性之知来接近圣人境界,进而理解圣人所作经典中蕴含的义理,这又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义理之学。注重德性实践,从德性出发去理解经典和圣人,最后通达“天理”,是二程经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两宋“道学”或“宋明理学”不同于传统儒家经学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儒家经典诠释思想与西方诠释学思想的差异所在。
在唐宋儒学转型过程中,河南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是承上启下的关键,陈来在其主编的《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一书中指出:“在历史的意义上,可以说二程是两宋道学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二程,周敦颐、张载、邵雍的影响就建立不起来;没有二程,朱熹的出现也就成为不可能。一句话,没有二程,也就没有两宋的道学。” (陈来主编,第3页) 此说切中肯綮。
关于二程的思想学说,学者多从儒学更新的大背景下展开分析,由此出现了“汉宋转向”“佛道影响”“先秦固有”“政治目的”等不同的解释,实际上,这四点在二程思想建构中往往是相互交织的。而对二程的经学思想研究,则大多着墨于两个转向:一是在解经方法上,由汉唐章句训诂之学转向义理之学;二是在经典文本重心上,由以《五经》系统为重转向以《四书》系统为重。
在经学解释层面,研究者基本沿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中汉学、宋学两分的论述来说明唐宋之际经学转向的主要特征。不过也有学者不满意这种分法,进而有三派、四派之说。 (见皮锡瑞,第3页) 但无论何种说法,都将二程经学界定为相对于章句训诂的“义理之学”。从经典文本重心的层面看,学者多重视二程的《四书》学,认为二程是通过《四书》来建构其理学体系的,这一过程被称之为“经学的理学化”。也就是说,将《四书》和《易传》作为二程发明“性理之学”的主要对象,而《五经》则颇难提供类似的资源。那么经学和理学的关系,就是以理学范畴来统领经学。
可以发现,以往对二程解经方法的研究有失之笼统之嫌,缺乏对德性层面的考察,以及忽视德性在理解、诠释经典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对“义理”含义的分疏也比较模糊,并未厘清《四书》的性质及其与《五经》的关系,这些都需要对二程经学的性质有一重新判断。本文试图通过对二程经学思想的梳理,揭出其经学诠释中的德性实践和德性之知两个维度,以说明二程经学思想之于汉唐经学的真正转向之所在。

一、训诂、义理、德性:经学诠释的三个层次
《四库全书总目》将经学传统分为汉学和宋学,周予同则认为应当归纳为三派,即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和宋学。这三派的特点,简明地说,今文学偏重于“微言大义”,古文学偏重于“名物训诂”,宋学偏重于心性理气。 (见皮锡瑞,第3页) 实际上,如果以经学解释看,古文学是注重文字训诂的,而今文学和宋学都注重义理解经,只是两者的“义理”取向不同。因而,简单地把汉学和宋学之分理解为章句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的区别,失之粗略。汉唐经学中也存在义理之学,如《刘歆传》曰:“及歆治《左传》,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班固,第1967页) 章句与训诂也有所分别,马瑞辰在《毛诗训诂传名义考》中说:“诂训与章句有辨。章句者,离章辨句,委曲支派,而语多傅会,繁而不杀;蔡邕所谓‘前儒特为章句者皆用其意傅,非其本旨’,……诂训则博习古文,通其转注假借,不烦章解句释,而奥义自辟;班固所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 (马瑞辰,第4页) 因而,章句较之训诂而言更具义理意味。赵岐的《孟子章句》就是采用义理阐释的方法。对此,《四库全书总目·〈孟子正义〉提要》云:“汉儒注疏,多明训诂名物,惟此注笺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古学稍殊。……盖《易》《书》文皆最古,非通其训诂则不明;《诗》《礼》语皆征实,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论语》《孟子》词旨显明,惟阐其义理而止。”四库馆臣的这种说法,大致不错。但《周易》何尝只是通训诂就可以明了的,《诗经》语固征实,但超出名物之外的发挥同样不少,更何况未提及的《春秋》学中尤重“微言大义”的《公羊》《穀梁》,所以,汉唐注疏大半与“义理”难脱干系。
唐宋之际对于前代注疏的批判,较之汉唐训诂之学一派,确实更偏重于义理之学。但与汉唐经学中的义理之学不同,宋儒对于义理之学的偏重,表现在他们特别措意于义理的统一,对汉儒烦琐的章句训诂以及门户相争导致的异说纷见尤为不满。虽然唐初通过官方定本达成经学的统一,但这仅是表面上的形式统一,其中的义理整合仍付阙如。如何才能对经典的义理进行更高层次的统一,寻找出儒家的“大义”之所在,是当时儒者共同的追求。与此相关,批判汉唐注疏的另一方面在于“义理”的内涵,同样是以义理形式来阐释经典,但“义理”的具体内容则可以相去很远。在经世致用和佛道思想影响下,北宋思想家大多融合各方面的思想义理,来塑造自己对传统经典的解释。
处在时代思潮的漩涡中,二程兄弟自不例外。但是,二程的经学转向具有重要的哲学史和学术史的意义,因为是他们在真正意义上进一步揭示出了经学诠释中的“德性”层次。对于二程而言,从章句训诂之学转向义理之学,不仅仅是解经形式上的转向,更为重要的是从德性实践角度来加以看待,即以何种“义理”来理解经典?诠释经典的目的何在?以及怎样才能真正理解经典中所蕴含的义理?
在二程语录中,谈及“义理”一词处有近七十条,二程使用“义理”一词的含义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泛言普通意义上的“道理”,如“然当时以为不宜取者,固无义理,然亦是有议论” (《二程集》,第49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若谓夫从役,妇便怨,成何义理?” (第357页) ;二是特指与其他思想相区别、传承孔孟之道的儒家经义,如“古之学者,皆有传授。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 (第13页) ,“尝语学者,且先读《论语》《孟子》,更读一经,然后看《春秋》。先识得个义理,方可看《春秋》。” (第164页) “或读书,讲明义理” (第188页) ;三是指道德体用意义上的“理义”,如“义理与客气常相胜,又看消长分数多少” (第4-5页) ,“皆彼自有此义理,我但能觉之而已” (第5页) ,“今之学者,惟有义理以养其心”。 (第21页) 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二程的“义理”不仅仅是指文本诠释意义上的,也包括道德本体、道德实践的意义。
因而,如果将二程的经学思想理解为“义理”之学,那么首先不是指解经形式上的义理诠释,而是指向德性实践的目的,即从经师之学、利禄之学向德性实践转变,这也是二程“道学”的含义所在。
“道学”一词,宋初柳开就已提出,柳开使用的“道学”,是相对“禄学”而言的:
学而为心,与古异也。古之学者,从师以专其道;今之学者,自习以苟其禄。乌得其与古不异也?古之以道学为心也,曰:“吾学,其在求仁义礼乐欤!”大之以通其神,小之以守其功,曰:“非师,吾不达矣。”去而是以皆从师焉。今之以禄学为心也,曰:“吾学,其在求王公卿士欤!”大之以蕃其族,小之以贵其身,曰:“何师之有焉?” (《柳开集》,第7页)
柳开的这一说法,与二程的经学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反对当时学者追求仕途利禄而不求仁义礼乐。利禄之学表现在经学上就是记诵之学,因为为学的目的在追求利禄,所以就不会真正去体悟经典中所蕴含的德性修养之义,经典只是通往仕途的敲门砖。这样治经的方式一定是强调章句注疏,注重记诵之学和文章之学。
承上所说,二程“义理之学”的一个重点在于实践目的层面,而汉唐经学中除了文本诠释之外,似乎也表现出实践指向。汉代经学无论是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还是名物制度的训诂,都与其政治上的关联分不开。汉代经学的现实影响在政治层面,这从汉儒的孔子为“素王”、作《春秋》、为汉“立法”的流行说法中可窥一斑。钱穆在《孔子与春秋》中说:“孔子在汉人观念中,是内圣而兼外王的,更毋宁是因其具备了外王之道而益证成其内圣之德的。所以孔子在汉代,要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古帝明王并列了。但唐以后的孔子,在人心目中,时时把来和佛陀与老聃并列了。换言之,这是渐渐看重了他的‘教’,而看轻了他的‘治’。” (钱穆,第292页) 实则经学的政治影响又多表现为关于礼制的争论。政治与教化分不开,廖平在《今古学考》中就认为汉代经学今、古文之分在于礼制。因而汉代的政治就是礼教或名教,极为重视“礼”对个人行为的规范,将礼教思想贯彻到实际政治操作层面,影响甚深。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乃至唐代。但部分儒家学者对汉唐礼制颇不以为然,如欧阳修就认为: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故自汉以来,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俯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末节也。 (欧阳修、宋祁,第307-308页)
欧阳修的思路仍是注重儒家的礼乐制度,不过他指的是三代的王政礼乐,而不是秦汉以后儒生“灾异谶纬”之说以及徒具形式的“礼之末节”。欧阳修认为,“礼义者,胜佛之本也”。 (《欧阳修全集》,第288-290页) 企图通过王政礼乐的教化来实现治道。但是欧阳修对于礼义的根源并未深究,其观念与汉唐儒生对于政治实践的看法大同小异。礼乐确实可以用来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可是所以能用来教化的根据则不在礼乐自身。不明白礼乐的义理不在于礼乐,就不可能让人从佛教的“深深之理”转向服膺儒家的“浅浅之教”。
与欧阳修不同,关于汉唐以来的礼教,二程明白指出:“后汉人之名节,成于风俗,未必自得也。” (第4页) “东汉士人尚名节,只为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贤也。” (第232页) “明理”才是儒家实现成圣成贤理想的关键所在,如果仅是行为上受礼制约束,而对于其内在根据不能深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则无法真正理解礼乐的意义。也就是说,尽管汉唐经学也强调实践,比如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和政治实践,但是这种实践的根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孔孟,这种阐释是否符合经典文本所昭示的意义,是有疑问的。二程认为,应当以孔孟之学来统一六经的“义理”,孔孟之学通过道统论的形式,主要展现在《四书》中,《四书》的义理就是孔孟的义理。因而从经学文本上说,不仅是从《五经》转向《四书》,而且是以《四书》来统领《五经》。这种统领又是以“德性实践”和“德性之知”为线索的。二程认为,《大学》是入德之门,《中庸》是传授心法,《论语》《孟子》是要约处。“要约处”的意思是《论》《孟》是圣人直接传授德性修养方法之书。以《四书》为《五经》之阶梯,就是指《四书》乃治《五经》之方法论,通过学习《四书》的义理并加以实践,进而使自身德性充其极,才能完全理解《五经》文本背后的圣人之意。
二程治经的转向主要在于德性,当然政治和礼制的层面也并未缺席,但是从原来的文字训诂、注重典章制度而对德性关注不足一变而为重点关注“礼而上”的德性修养,尤其是探讨如何“就身上做工夫”的方法,则是毋庸置疑的。二程《遗书》中有一段话充分体现其经学思想:
苏季明尝以治经为传道居业之实,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质之两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辞立其诚’,不可不子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若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乃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正叔先生曰:“治经,实学也。……如《中庸》一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识达,所得多矣。有虽好读书,却患在空虚者,未免此蔽。” (第2页)
这段材料同时记载了明道和伊川对于治经的看法,从内容看,二程的经学理念大致相同,他们都认为治经是“实学”,讲习也是“实学”,看学者如何对待。明道认为,不管是治经还是讲习,主要目的是“进德”,修其言辞要立己之诚意,“进德”以“忠信”为下手处。伊川则认为治经是领会经中之“道”,通过圣人所作之经,不仅可理解历代圣人治国理政的事迹,而且也可下学而上达。从经文中可了解古圣贤的行为处事,从中探求圣人的用心,目的都是自身的德性修养。程颐在解释《周易·大畜卦》时说:“人之蕴畜,由学而大,在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识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义也。” (第828-829页) 同时,伊川更强调治经要“自得”,如果不是“心得识达”之人,没有相应的德性能力去领会圣人作经的用意,只是盲目读书,以训诂注疏为重,是无法和圣人契合的,对经典所蕴含的义理也不能心领神会,结果是治经没有实得,不免空虚。
治经以德性为目的,这实际就是回归孔子的本义。孔子面对三代圣王留下来的典籍文献,从德性的角度来整理删定六经,统一了六经义理,形成儒家的“六艺之教”。退一步说,即使六经并非由孔子删定而成,也是明显笼罩在孔子所创的儒家学派思想之下的,这是六经的义理源头。虽然对于“六艺之教”的具体施行,不同的弟子和后学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个德性实践目的是先秦儒家所共有的。而汉唐经学被批判为是章句注疏之学、记诵之学、利禄之学,则与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二程实际上想重回先秦儒家的经学传统,以道德体用意义上的“理义”来理解经典:“学者必求其师。记诵文章不足以为人师,以所学者外也。故求师不可不慎。所谓师者何也?曰:理也,义也。” (第323页)
因此,如果用“义理”之学来概括二程的经学思想,那么对于“义理”的含义必须作出分疏。“义理”的含义可以从形式、内容和目的三个方面来理解,从形式上说,“义理”是相对于注重名物训诂来注解经文的另一种解经形式,其特征是阐发经文所蕴含的道理。从内容上说,“义理”有不同的意义,一是指汉代今文学所阐释的“微言大义”;二是指在佛道思想影响下以老庄、佛学的“义理”来阐释经文;三是指回到圣人之道,以孔孟思想为依归所作的“义理”,这个“义理”不仅仅是文本所有的字义和道理,而且指向本体意义的天地之理。从目的上说,“义理”指的是相对于讲授注疏、记忆文句的讲师、经师之学,向“就身上做工夫”的儒者之学转变,儒者之学的目的就是修养自身德性,注重道德践履。在这个意义上的“义理”就不只是解经层次上的,而是实践意义上的“德性”。

二、“德性之知”的奠基性作用
二程对于汉唐经学的批判,一方面是认为汉唐儒生没能真正理解圣人作经的用意;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之所以不能真正理解圣人用心,是因为他们并未从自身德性出发来理解圣人的经典。或者说,由于他们本身的德性涵养不足,无法完全领会经文中所蕴含的圣人用心。
“六经”的文本有两层来源,一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王的行事著录;二是经过了圣人的删定,《尚书正义》中说,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第10页) 这两层来源奠定了六经文本中蕴含的德性义理。六经文本的义理不仅为了学者的德性修养,同时也需要具有相应的德性才能得以真正理解。
隋代王通就认为六经的义理有深浅层次,因而学习经典的次序也有先后,其先后的依据在于人的德性程度,《中说·立命篇》中说:
姚义曰:“尝闻诸夫子矣:《春秋》断物,志定而后及也;《乐》以和,德全而后及也;《书》以制法,从事而后及也;《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或曰:“然则《诗》《礼》何为而先也?”义曰:“夫教之以《诗》,则出辞气,斯远暴慢矣;约之以《礼》,则动容貌,斯立威严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辩其德。志定则发之以《春秋》,于是乎断而能变;德全则导之以《乐》,于是乎和而知节;可从事则达之以《书》,于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则申之以《易》,于是乎可与尽性。”……子闻之,曰:“姚子得之矣。” (见张沛,第232-233页)
六经的学习次序以《诗》《礼》为先,然后再学《春秋》《乐》《书》《易》,原因在于每部经典对于人的德性培养起不同的作用,先学《诗》《礼》可以使人的言行德志有较好的基础,在德行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再来学习其他经典,才能充分理解经典所蕴含的义理,使经典的作用真正发挥。
德性修养的不同导致了学者在理解圣人作经意义的程度上的差异,这是重要的起点。以《论语》的“性与天道”章为例,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如何解释“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传统上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圣人不说天道性命这种玄虚之事,所以子贡这些弟子都不能听闻。如桓谭《上光武疏》云:“观先王之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而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 (见范晔,第959页) 二是圣人关于天道性命的学问非其人则不传,如《史记·天官书》云:“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 (司马迁,第1600页) 三是认为孔子所说的性与天道的学问太深奥,子贡无法理解。如《论语注疏》:“子贡言,若夫子言天命之性,及元亨日新之道,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闻。” (何晏注、邢昺疏,第110页)
对此,二程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性与天道,此子贡初时未达,此后能达之,故发此叹辞,非谓孔子不言。” (第353页) 按此解,“性与天道”章所要表达的,并不是圣人不说“性与天道”,也不是不传子贡“性与天道”,而在于子贡本身德性能力的高低。子贡一开始德性不足,难以理解圣人之言,即“初时未达”状态;后德性精进,能理解孔子“性与天道”的含义了,所以发出叹美之辞,这就是“达”与“未达”的区别。实际上,二程之前的皇侃在《论语义疏》中的说法就颇可玩味。皇氏在“夫子之言”处断句,即“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认为“夫子之言即谓文章之所言也。……言孔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见,而六籍所言之旨,不可得而闻也。所以尔者,夫子之性,与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致此处深远,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闻也。” (皇侃,第110页) 这是从孔子的“德性”出发,有德然后有言,要理解有德之言,就需要自身德性与其匹配。
这里还可通过颜渊与子贡对比,更直观地感受这种状态。与子贡不同,颜渊一开始就能领会圣人之意,“不违如愚”,“亦足以发”。颜渊之所以能“不违如愚”,是因为完全跟得上孔子的思想;之所以能“发”,是因为真正懂得孔子思想而加以应用。前者是理解,后者是实践,这是“学”的真正境界。子贡自己很了解这种差距,认为自己是“闻一以知二”,而颜渊则“闻一以知十”,“十”较之“二”,并不仅是数量上的差距,更是质的不同。所以,在知性层面,以子贡的聪颖,未必不如颜渊;但在德性层面,两者就有不小的差距。如果以“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来比方,子贡的“闻一以知二”之“知”是“闻见之知”,那颜渊“闻一以知十”之“知”则就是“德性之知”了。
传统的解释主要从孔子角度看,二程是转移到子贡的角度来看。由于解释者理解程度的差异,导致对圣人思想的领会不同,“这个义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鲜矣’。此个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见”。 (第42页) 道是同样一个道,不多不少,但仁者、知者和百姓对于道的认识就完全不同,这就说明问题不在于对象或者作者,而在于理解者自身。
二程弟子谢良佐在《论语解序》中说:
余昔者供洒扫于河南夫子之门,仅得毫厘于句读文义之间,而益信此书之难读也。……唯近似者易入也。……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读之,谓终身可行之恕诚何味。方其胁肩谄笑,以言人者读之,谓巧言令色宁病仁。未能素贫贱而耻恶衣恶食者读之,岂知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乐。注心于利,未得而已,有颠冥之患者读之,孰信不义之富贵真如浮云……唯同声然后相应,唯同气然后相求。是心与是书,声气同乎?不同乎? (见黄宗羲,第927页)
上蔡的说法颇得二程经学要义,《论语》不像老庄那样谈天语命,伟词雄辩;也不像司马迁、班固那样文辞雄深雅健;更不像《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能愈疾引年。但是如果从这些角度去理解圣人所作的经典,则根本无法领会圣人用心,因为圣人作经用意本不在此。只有自身德性能力不断接近圣人境界,才能了解经典中蕴含的真义,这也就是“唯近似者易入”。同时,经典也具有某种印证的作用,经典本身具有的权威性和固定性,可以范导德性修养方向,使之不至于汗漫流荡。通过治经来修养自身德性,又以德性之知来增进对经典的理解,“书与人互相发也”,问学与德性是相须为用的。

三、德性之知的含义
从自身德性出发去理解经典,可称为“德性之知”。“德性之知”既不同于“见闻之知”,也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认知”。“德性之知”的认知对象是“性与天道”,一方面它不局限于耳目所及,另一方面它具有道德意义。“德性之知”不是固定而是发展形成的,是通过自身道德实践和自我反思,逐渐达到理想状态。对于一般人而言,“德性之知”是未完成状态,通过不断修养,接近圣人的境界。通过“德性之知”才能真正理解经典的意义。
首先,“德性之知”具有自得性。二程非常重视为学要“自得”,在语录中就有二十多条谈及“自得”。其“自得”大致有三层意思:一与“德”相关。“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诸己,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虽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窥测见其一二,得而用之,乃自谓泄天机。” (第14页) “德者,得也,须是实到这里须得。” (第42页) “自得”就是自身的实实在在的德性,通过读书明理不断修养而成,“学莫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第316页) 德性是由内而外而发的,就是要自己能够信得及、自己受用,对于经书中所说的道理能够实实在在地体会,而不是虽然认知到有这个意思,但自己却还没有完全认同。“实理者,实见得是,实见得非。凡实理,得之于心自别。若耳闻口道者,心实不见。若见得,必不肯安于所不安。……得之于心,是谓有德,不待勉强,然学者则须勉强”。 (第147页) 明道说的“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也是这个意思。一与“道”相关。“自得”的对象往往是“性与天道”而不是一般耳目所及的事物,“性与天道,非自得之则不知,故曰‘不可得而闻’”。 (第361页) “如此等,则放效前人所为耳,于道鲜自得也。” (第194页) “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当自得之。” (第136页) 就是说“性与天道”这种“形而上者”必须是德性“自得”才能认识的,因为“形而上者”非具体可见,不像形下之器,耳目之官无法听闻,也无法通过他人的言说而获得,所以需自身内在德性不断修养才能体贴。而且也只有认识到这种天理,才算是真正的“自得”。第三是“学”的根本方法。“同伯温见先生,先生曰:‘从来觉有所得否?学者要自得。《六经》浩渺,乍来难尽晓,且见得路径后,各自立得一个门庭,归而求之可矣。’伯温问:‘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圣”,须是于思虑间得之,大抵只是一个明理。’” (第296页) 治经问学要“自得”,就是指“各自立得一个门庭”,门庭主要是指心有主见,这个主见不是随心所欲地解释,而是与天理相通,“自得”要“思”,就是要自立吾理。德性的对象是“天理”,自家真正体贴到“天理”后,使“德性”不断充实,心得识达,“自得”然后治《五经》,才能实有所得。
其次,“德性之知”具有实践性。一方面,通过亲身经历、实践、体验后,有了对所认知的事物的真切认识,增进自身德性修养,才能对经典之言有真正的理解。为学要知之,又要体之。“学为易,知之为难。知之非难也,体而得之为难。” (第321页) 随着自身德性的增进,对于经典的理解也逐渐加深,“某年二十,解释经义,与今无异,然思今日,觉得意味与少时自别。” (第187页) “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论语》,有读了后全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第261页) 这种加深显然不是指文本字句上的理解,而是对于经典所要真正指示的超越文本之上的义理的体贴。
这里的实践还突出强调德性的践履,二程曾批评王安石:“公之谈道,正如说十三级塔上相轮,对望而谈曰,相轮者如此如此,极是分明。…… (二程) 直入塔中,上寻相轮,辛勤登攀,……至相轮中坐时,依旧见公对塔谈说此相轮如何如何。” (第5页) 二程与王安石的区别就在于同样谈经论道,但是二程是真真实实深入到儒家之道的内部,去实实在在践履圣人所说的道德工夫。这样得来的感受是完全不同于在外自私用智,仅得依稀仿佛,只有经过实践的知才是真知。
另一方面,也通过落实到平常实践中的行为来检验是否真的理解经典的意义。“今人不会读书。……须是未读《诗》时,授以政不达,使四方不能专对;既读《诗》后,便达于政,能专对四方,始是读《诗》。……须是未读《周南》《召南》,一似面墙;到读了后,便不面墙,方是有验。大抵读书,只此便是法。如读《论语》,旧时未读是这个人,及读了后又只是这个人,便是不曾读也。” (第261页) 治经问学的目的在于自身德性修养,德性不只是道德规范的遵守,也是处事得宜的能力,在人伦日用中展现德性的力量才是治经问学之根本所在。
再次,德性之知是理解性而非建构性的。“德性之知”对于解释经典文本来说,是从理解的角度来进行的,将经典文本作为意义的承载者,以理解其中蕴含的意义为目的,还是从自身可以赋予文本以新的意义,即建构性,来看待经典文本,这是“德性之知”的性质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温伟耀在其《成圣之道》一书中,尝试运用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去整理和消化二程的哲学思想,强调亚里士多德关于科技知识 (technical knowledge) 与道德知识 (moral knowledge) 之间的界分,“对于伊川,我们将会用哲学诠释学的角度去理解他的格物致知工夫” (温伟耀,第19页) ,认为“每份文献的背后都有一份生命体验,而文献就是这人类心灵所展开的世界和这生命体验外在化的呈现。故此诠释者与文献的相遇,并非只是主体与无意识存在物的相遇,而是主体心灵 (诠释者) 与另一主体心灵 (文献的原作者) 之间‘视域的融摄’”。 (同上,第16-17页) 因而,“一方面,道德修养的工夫必然地连起主体生命的体验,故主体在理解过程中的主观参与性一定较其他题材为高。另一方面,宋明儒学者自己对诠释经籍的立场和方法,也是视文献为提升自我道德生命体验的一种指点和启迪,诠释的目的并非旨在抽出文献原作者的本意而已,而是将自己的体验结合在诠释的历程之中,结果就是透过对典籍的诠释去把捉更丰富的道德生命体验。” (同上,第18页)
借鉴西方诠释学来研究二程思想,进而有意识地把握道德修养工夫和主体生命体验对理解经典文本的意义,对二程思想的把握有一定帮助。不过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有囿于西方诠释学框架处,温氏对于二程经学思想的理解同二程的本旨是有出入的。首先,由于受到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影响,认为解释者的理解可以丰富文本的意义,或者说文本的意义恰恰在与解释者的互动中逐渐完成。这一观点与中国传统经学是不合的。在二程而言,读经的意义在于领会圣人作经之意以及经中所蕴含的圣人之道,这一圣人之道本身是完满的,是不待解释者的理解就自身具足的。学者和圣人的德性就本然状态来说,是相同的。之所以不能完全理解经典的意义,主要在于学者自身德性不足。一旦学者的德性能够完善,达到圣人的境界,就能领悟圣人所作经典的意义,而领悟到的意义并非超出圣人之意以外的义理。其次,同样地,学者的主体生命体验对于经典的诠释也并非是增加、丰富其义理,而是不断接近其原有的含义。学者的生命体验应该同圣人格物、明理、作经的实践相靠拢,以此才能完全把握到圣人的用心。
需要注意的是,二程对于经典的看法以及在解释经典过程中所持有的主观态度,与其最后导致的客观效果,并不能混为一谈。二程对于圣人所作经典的看法,在现代学者看来可能是过于肯定的,但这对于传统儒者而言却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二程在解释经典时是以传承圣人之道自任,而并非在圣人之道以外有其他创新。至于从研究者来看,二程所诠释的思想不同于孔孟的思想,对于二程思想的这种解读也可以是见仁见智的,如有学者就认为二程发明的义理之学乃先秦固有的,最符合孔孟之道。
最后,德性之知的根据在于“天理”。对于汉唐经师的注疏,二程认为其并没有真正理解经文意义,由于“秦火”之后,经籍散佚,汉唐儒生对于先秦经典的理解多有错谬。可是到二程的时代也没有重新发现先秦文献的原本,就文本而言,二程与汉唐儒生基本是一样的。那么如何断定经文的原意和圣人的用意,这里的标准是什么,又在哪里呢?汉代今文经学的可靠性主要在于自身的师说传承,因而严守师法、家法是他们解释经文的根据。古文经学则依赖后来发现的古文献,如孔壁古文,这是他们拥有经文解释权的根据。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说:“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以远矣。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孝成皇帝愍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或脱编。……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 (见班固,第1969-1970页) 可以看到,对于经典文本解释权的争夺,最终须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根据。
二程的解经根据是哲学的,既不是师传家教,也不是出土文献,而是“理”的一致性。六经的形成,一是三代圣王的行事著录,一是经过孔子整理删定。前者是圣王治理国家、教化人民的事迹,呈现出圣王对天地万物、人事变迁之理的理解,后者是圣人从德性角度对先代文献进行整理,其中包含了圣人之道的真正意义。由于“性即是理”,后学通过格物明理,修养德性,进而理解圣人作经的意义。如果自身德性不足,就不能真正领会圣人作经的意义,如不能通达“天理”,就无法完全理解经典中的义理。后学理解经典文本含义的可能性与“圣人可学而至”的理念是统一的,圣人可以通过努力修养而达到,那么圣人作经的用心自然也可以通过学问思辨而理解。
因此,理解经典就需要从自身德性出发,德性之知的根据是“天理”。一方面,圣人作经是有德者有言的自然作为,治经应当从自身德性出发来理解经典,人的德性来自天理,天理是一致而稳定的,因而理解圣人所作之经的根据在于天理;另一方面,圣人作经的本意是“明理”,在经典中蕴含天地万物之理,治经的目的是因经典之言而求圣人之意,因圣人之意而达天地之理。只有通过“德性之知”才能理解经典之言,领会圣人之意,通达天地之理,“道之大原在于经,经为道,其发明天地之秘,形容圣人之心,一也”。 (第463页)
四、结语
一般而言,诠释关涉作者、文本、读者三个方面。传统的经学诠释分为章句训诂和义理解经,无论是训诂还是义理,所注重的对象是作者和文本,即着重理解文本的字句意思以及领会作者透过文本所要表达的道理。而读者的意义则往往难以确定,一方面,读者是作者和文本的传达对象,读者通过不同的方法尽可能地理解作者的原意和文本的本义;另一方面,读者同时又参与了义理的诠释,甚至是文本新义的建构。就前者而言,读者作为接受者,其重心在于作者和文本,而存在的问题是真正完全理解作者和文本如何可能?如果是后者,读者不再被动,而是文本意义的塑造者,重心就转移到了读者,读者所获得的不只是知识的累积,同时也是与作者对话,更进一步地将其应用于实践之中,使得自身的理解不断发展。
然而对于传统儒者而言,经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文本,而作经的圣人也不是普通的作者。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作者和文本诠释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传统经学。如果将经典作为普遍的文本,一来在诠释文本时只注重对文字章句、名物制度的训诂而没有体会圣人的用心所在,二来尽管脱离了烦琐的训诂而转向义理解经,也往往可能自私用智、附会穿凿,用其他不合的义理来诠释经典,如二程认为王弼以老庄解《易》。这些都是二程所要批判的,也是二程经学诠释思想之于汉唐经学的转向所在。二程经学思想不只是义理之学,更是德性之学,包含了德性实践和德性之知两个维度。二程将诠释的重点从作者和文本转向读者,将治经问学的目的从知性理解转向德性实践,这是脱离了形式上的训诂之学。同时,又指出要以德性之知来接近圣人的境界,进而理解圣人所作经典中所蕴含的义理,这就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义理之学。可以说,注重德性实践并且从德性出发去理解经典和圣人,最后通达“天理”,是二程经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两宋“道学”或“宋明理学”不同于传统儒家经学的关键所在。当然,更是中国儒家经典诠释思想和西方诠释学思想的差异所在。
不过,依上述理路,二程经学诠释思想就面临一个疑难。二程提倡由经穷理,又提出格物穷理的工夫,这样,穷理明德工夫就有两种途径,由经穷理和格物穷理,两者并不排斥,因为在二程而言,格物中也包含着读书治经这样的实践。但如前所述,如果治经问学的目的是德性修养,而德性修养除了治经外还有其他的途径,或者说是更好的更直接的方法,如对天地万物、人伦日用中所蕴含之理的穷究,那就会导致治经问学在德性修养中的地位的减弱甚至被抹杀。这一点恰恰是后来经学与理学之间紧张关系的滥觞。朱熹、陆九渊关于“尊德性”“道问学”之争,在王阳明那里“良知”不仅是理解经典的出发点更是判断经典的权衡,这都是二程经学诠释思想疑难在不同背景下的表现。
供稿: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