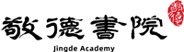董仲舒司法思想新探
作为汉代的一个经学大师,董仲舒的思想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董仲舒的司法思想是其法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一直未见专文对其予以探讨。笔者拟在此方面略作尝试,探讨一下董仲舒司法思想的具体内容及其对汉代司法制度的影响。
一、董仲舒司法思想的理论根据及对国家司法权的定位
董仲舒司法思想的理论根据是天道论和人性论,天道论是形而上的根据,人性论是形而下的根据。他说:“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又说:“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他认为,天有阴阳二气,阳主生,阴主杀,阳为“天德”,阴为“天刑”。如其所言“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又指出:“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春秋繁露·基义》)天的本性是亲近阳气而疏远阴气,实际上也就是亲近德而疏远刑。董仲舒还说:“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辩在人》)“阳贵而阴贱”的意思也是说天贵德(阳)而贱刑(阴)。根据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理论,天与人之间有密切关联,只有效法天道,人间社会才会趋于正常和健康。那么,根据天“贵阳贱阴”的逻辑,人间的政治生活与法律生活应当是“贵德贱刑”或“德主刑辅”。《汉书·董仲舒传》所引董仲舒之言“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正说此意。
董仲舒说:“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志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如此看来,“人”只不过是缩小了的“天”,而“天”不过是放大了的“人”而已。这样一来,天的特性自然就是人的特性,天的规则自然也就是人的规则了。正如董仲舒另外所说:“天人之际,合二为一,同而通理。”(《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既然“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因此,人类社会自然也应该“好德不好刑”。当然,不好刑并非不要刑,但刑应当处于辅助德的地位上,这就导向了“德主刑辅”说。正如董仲舒所说:“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春秋繁露·天辩在人》)这就是说,一种符合“天道”的治国模式应该是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董仲舒还指出:“以德为国者,甘于饴密,固于胶漆。”(《春秋繁露·立元神》)这是进一步强调了德治的重要性。如果将刑罚置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上,那就违反了自然规律。董仲舒说:“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犹阴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又说:“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春秋繁露·阴阳位》)“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春秋繁露·基义》)“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春秋繁露·基义》)可见,德主刑辅合乎自然规律,而刑主德辅则违反了自然规律。

学者指出:“董仲舒在德、刑之间倡导以德为主,这是对孔子导德齐礼、孟子善教得民心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无疑比专任刑罚要宽恕,也是对汉武帝时期严刑峻罚的强烈批评。”笔者认为,这一评价是中肯的。根据董仲舒“天人相类”的观点,人与天在外形和本质等方面均相类似,所谓“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之副在乎人”(《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正言此意。人是天的副本,在人性方面也是如此,人性的善恶对应着天的阴阳,并以天的阴阳作为其根据。如其所云:“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他还提出了着名的“性三品”说,将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但又称“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实性》)。实际上,根据董仲舒的人性理论,具有圣人之性(天生的道德完善之人)和斗筲之性(天生的道德败类)的人都是极少数,可以忽略不计,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具备中民之性的人,故中民之性又被称为“万民之性”。
按照董仲舒的说法,中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尽善”,要实现德性的完善需要接受后天的道德教化,从事道德修养。他说:“今万民之性……可谓有善质,而不可谓善。……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又说:“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之以仁义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又说:“性者,天资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春秋繁露·实性》)而对不愿接受教化且肆意作恶者,则进行必要的惩罚,因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法度自然不可完全弃而不用。董仲舒指出:“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谊,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汉书·董仲舒传》)上述人性理论实际上为其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提供了一种理论根据。
有学者指出,董仲舒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善须王教而成”的主张。他强调靠礼义来节制人的情欲,称“好色而无礼则流,饮食而无礼则争,流争则乱。故礼,体情而防乱者也”(《春秋繁露·天道施》),并“把善须王教而成,同性有善端的思想结合起来……性是天资之朴,善是王教而成,离开天生资朴之性作基础,圣王的教化作用就不可能实现;离开王教的作用,天生资朴就不可能转变为现实的善。而注重德教,是孔孟共有的思想,讲性有善端,又是孟子的思想,因此,董仲舒的善需王教而成的理论又包含着孔、孟的思想成分”。
也有学者认为,董仲舒的人性理论区分了可能性与现实性,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人性中善的可能性才会变为现实。所谓“性待渐于教训而后为善”即指此言。“……圣人之性、斗筲之性都不是他所说的质朴之性,也就不属于他所要讨论的范围,而只有这种有善质尚未为善,经教化可以引导为善的中民之性才是他要讨论的性。这里,董仲舒把‘性’分为三类,实际上是对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的继承与综合,但他对‘性’的理解与孟荀有很大区别。……董仲舒则认为他所要说的‘性’本身是自然质朴的,它仅仅包含着可能为善或为恶的根据与可能,而要去除人性中这种潜在的恶,实现其可能的善,还得依靠后天的教化、培养。因此,在他看来,探讨‘性’的问题,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明确如何才能使人性实现善,完成善,达到圣人之性”。上述说法颇有道理。董仲舒的人性理论既是其道德修养理论的基础,也是其预防犯罪策略的理论根据,因为人性的不断完善是人逐步摆脱犯罪诱惑的关键。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为其“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预设了一个形而上的根据—“天”论和形而下的根据—人性论,并在论述其治国方略的过程中明确了国家司法权的定位—辅助道德教化,由此而阐释了他的司法思想:国家司法权的行使必须符合道德要求、体现道德精神并对德教起辅助作用—这就是“德主刑辅”的意思,此处之“刑”当然包含了刑事司法的含义。董仲舒虽然主张“性待教训而后能善”(《春秋繁露·实性》),要求统治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但他从来也没有完全否定“刑”(包括刑事司法)的作用,而只是强调了“刑者德之辅”即刑事司法的辅助地位。正如自然界中有“阴”的力量一样,人间社会也必须有“刑”(含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力量,这才体现“天人相类”的特点;而对普通人性来说,皆有“贪”、“仁”两种品性,如果没有刑事司法的威慑力量存在,将会使人放纵贪欲而日趋邪恶,故必须“设刑以威之”。因此,国家司法权的功能不仅是禁人为恶,而且也能驱人向善—因为拒绝向善者必然面临严重的司法后果。这就是董仲舒司法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二、董仲舒推崇的司法原则:“原心论罪”
《春秋繁露·精华》云:“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这就是着名的“原心论罪”原则。“听狱”是断狱或审判的意思,“本其事”是指考察犯罪的客观事实,“原其志”是指考察犯罪的主观动机,“志邪”是指动机邪恶,“本直”是指犯罪者一贯表现良好。“首恶”指首犯,根据《盐铁论·周秦》所谓“闻恶恶止其人,疾始而诛首恶,未闻什五之相坐”的说法,可知“首恶者罪特重”是针对连坐规定而言,反对株连无辜。引文大意谓根据《春秋》经义断狱,要求既考察犯罪的客观事实,又考察犯罪的主观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未能实施犯罪,也要进行惩罚;对犯罪团伙的首犯要从严惩处(对胁从宽免);对表现一贯良好而偶然犯罪的人可从轻论处。
有的学者对上述引文解释道:“‘本其事’就是以犯罪事实为根据,由此追查犯人的思想动机和目的,也就是‘原其志’。在这里董仲舒提出了一套内容丰富的断狱思想:(1)从犯罪行为所构成的犯罪事实出发,分析考察犯罪人的思想动机和目的。如果既有犯罪行为,又有犯罪动机目的,就构成了故意犯罪,应予从重处罚;如果只有犯罪行为,而无犯罪动机目的,虽然也构成犯罪,但只是过失犯罪,应予从轻处罚。这样,董仲舒就从犯罪人心理的深度,把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明确区分开来。(2)只要有犯罪动机目的,即使没有实施全部犯罪行为和最后完成犯罪,即犯罪预备、未遂、中止,也要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也就是说,既惩罚犯罪的完成形态—既遂,也惩罚犯罪的未完成形态—犯罪预备、未遂和中止。(3)在共同犯罪中,应从重惩罚首犯,即对首恶与从犯予以区别对待。”这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原心定罪”说的理解。
也有学者指出:“原心定罪的实质,是强调根据犯罪的动机、目的、心理状态等主观道德要件来定罪量刑。而衡量一个人动机、目的是否正当,是‘本直’还是‘志邪’的主要标准,则是儒家提倡的宗法伦理道德。这些伦理道德就是儒家经典中的所谓‘微言大义’。儒家通过引经决狱、原心定罪,不光是将经典置于法典之上,而且是将伦理道德置于法律规范之上,以达到以伦理率法,以伦理改法,并最后制定出符合伦理的法。引经决狱或《春秋》决狱与原心定罪是同义语。引经决狱是事情的现象,即决狱时引的是经而不是法律;原心论罪是事情的实质,即以行为人的行为动机、目的是否符合经义来决狱定罪,以行为人之‘心’,亦即主观道德的善恶来决狱论罪。”该学者进一步指出:“在我们所见的汉代引经决狱的案例中,有这样一种趋向:属于一般平民的基本上都是出罪,即从轻判决;属于皇亲国戚的则以‘君亲无将’为依据来严以执法。这样做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对引经决狱、原心论罪必须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第一,引经决狱无疑破坏了当时的法制,但问题在于破坏的是什么法制。秦代法制以严酷着称;汉承秦制,严刑酷法循而未改。引经决狱将经置于律之上,目的就在破坏当时的严酷之法。例如,当时的法律由族刑、连坐,‘恶恶止其身’这一条经义正好与之相反。第二,‘原心论罪’要求分清犯罪的过失和故意、一贯和偶然,要求在定罪量刑时考虑犯罪人的行为目的、动机和心理状态,作为一种刑法思想,是进步的。它的弊病在于过分强调犯罪的主观因素,而忽视甚至无视犯罪的客观事实,从而使人把握不住决狱的标准,会造成冤假错案,也不能避免酷吏‘因缘为市’。”上述说法有助于我们从司法的角度加深对“原心论罪”的理解。
从古籍中有关“春秋决狱”的案例看,基本上都对当事人作了轻缓化处理。以下是相关案例: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
君猎得麑,使大夫持以归,大夫道见其母随而鸣,感而纵之。君愠,议罪未定,君病恐死,欲托孤,乃觉之,大夫其仁乎,遇麑以恩,况人乎,乃释之,以为子傅。于议何如?仲舒曰:君子不麛不卵,大夫不谏,使持归,非义也。然而中感母恩,虽废君命,徒之可也。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袅首。论曰:臣愚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父而卒,君子原心,教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
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业,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决于事,皆无罪名,不当坐。
以上案例的处理结果基本上都是“不当坐”,即不对当事人进行刑事制裁,反映了司法上的宽和态度。“《春秋》决狱是在汉武帝时儒家思想已确立其统治地位,而封建法制又不完备的情况下盛行起来的。当时由于儒家提倡的礼治原则与司法实践之间存在不少矛盾,所以需要用经义决狱的方式加以调整。此风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封建法典彻底儒家化才最后终止”。
应该说,从整体倾向看,董仲舒的“原心论罪”还是兼顾了犯罪事实与犯罪动机,只是在涉及伦常犯罪时比较强调考察犯罪者的主观动机,即从道德的角度衡量其动机是否邪恶,如果动机邪恶,即使并未完成犯罪也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如果犯罪者一贯品行端正,仅仅是初犯,则可从轻论断。如此看来,董仲舒的“原心论罪”似乎无可厚非,与所谓任意出入人罪的后世恶评似乎并无所涉,何况董仲舒主张“赏不空行,罚不虚出”(《春秋繁露·保位权》)以及“务德而不务刑”(《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等等,其所著《春秋决狱》所收案例也多为刑罚宽免之事。因此,可以说“原心论罪”这一司法原则至少在董仲舒手上并未产生严重副作用,但司法实践中酷吏借用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任意出入人罪则有可能,如《盐铁论·刑德》所谓“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显然属于“原心论罪”原则的过度运用而产生的流弊。
三、董仲舒司法思想的价值取向:人道与和谐
董仲舒认为,司法是辅助教化的,而教化的价值目标则是人道与和谐。他说:“故折狱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狱而非也,暗理迷众,与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以不相顺,故君子重之也。”(《春秋繁露·精华》)将“教”(道德教化)当成“政之本”,将“狱”(审判执行)当成“政之末”,实际上是对“德主刑辅”的另一种表述。把德教当成政治的根本,把司法或刑罚当成政治的补充,这在当时的政治语境里与片面强调靠法律的威慑力治国理政相比具有更多的人道内涵。董仲舒在此提出了“折狱而是”的主张,强调司法审判必须符合“是”即公正与人道的标准,这样的司法才能有益于辅助教化。他推崇“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矣”(《春秋繁露·俞序》)的政治局面,认为好的司法可助成这一局面。
董仲舒认为,司法公正不仅符合“仁”道(人道),也会促成社会和谐。他要求那些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必须“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春秋繁露·离合根》)。不以喜怒赏罚才能使司法公正,才能使司法活动体现“仁”的精神,而这一精神又是“泛爱群生”的表现。用今天的标准衡量,所谓的“仁”或“泛爱群生”均指一种博大的爱心,是人道精神的反映。
董仲舒指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司法权的行使不仅必须辅助道德教化,而且本身也必须受道德的主宰,否则司法权就会变成一种盲目的力量,会破坏仁道、危及社会和谐。他说:“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虽曰权,皆在权成。是故阳行于顺,阴行于逆。逆行而顺,顺行而逆者,阴也。是故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阳出而南,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故曰: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经而后权,贵阳而贱阴也。是故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的观念论证了“大德小刑”、“务德而不务刑”的主张,强化了国家司法权的行使必须辅佐德教并符合道德原则(“刑反德而顺于德”)的理念,旗帜鲜明地反对“为政而任刑”的司法残暴主义,体现了一种深刻的人道精神。
在董仲舒的思想中,“仁”是一种爱心的反映,具有明显的人道色彩。他从天人合一的立场出发,认为人之“仁”来源于天之“仁”。他说:“仁之美者在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人之受命于天,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于天之尊,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逆顺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而博,唯人道为可以参天。”(《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董仲舒说这番话的目的就是指明人道与天道的相通性,这一相通性在于“仁”,从而为“仁”这一人道价值提供了形而上的神圣根据。董仲舒在该篇中进一步指出“天常以爱利为意”,而“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既然人间之王意在爱护百姓,当然在司法上要体现出宽和之风。
有学者评价道:“董仲舒以德教为主,量刑从轻,狱疑予民,胁从不罪,反对连坐、族诛,适时赦免,‘去奴婢,除专杀之威’,特别是《春秋决狱》,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应该说是可信的。那么,这无疑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的安定,有利于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这同当时的滥刑、乱杀相比,的确是一种爱民和进步。”如其所云,董仲舒的上述主张均体现了一种仁爱的精神,反映了董仲舒司法思想的人道价值。
董仲舒说:“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又说:“中之所为,而必就于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在董仲舒看来,由“中”致“和”,中和不但是自然法则,也是圣人治国理政的法则。所谓“以中和理天下”,就是按照中和的原则治理天下,包括在立法、司法中贯彻中和原则,从而促成社会和谐。
董仲舒又指出:“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后发德,必先平然后发威。此可以见不和不可以发庆赏之德,不平不可以发刑罚之威。又可以见德生于和,威生于平也。不和无德,不平无威,天之道也,达者以此见之矣。……虽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后发刑罚以立其威。”(《春秋繁露·威德所生》)董仲舒认为,统治者应效法自然法则,治国追求和谐,司法追求公平,要明白“德生于和,威生于平”的道理,为国家的政治生活营造和谐、公平的氛围,达到“世治而民和”(《春秋繁露·天地阴阳》)的理想目标,使国家长治久安。
综上所述,董仲舒根据阴阳五行的理论,系统论述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并对国家的司法权进行了定位,那就是辅助德教的实施并对德教加以保障;另外,司法权本身也必须受道德的制约,行使司法权力者必须有良好的道德自律能力,如此才能防止司法权变成一种盲目的非理性力量。董仲舒推崇的司法原则是“原心论罪”,该原则的实质在于将道德引入司法审判,对于一个道德上一贯表现良好的人来说,他的偶然犯罪往往并非因为其主观恶性,而是一时糊涂或认识偏差所致,故对其从轻论断是适当的;而强调对“首恶”的严惩,实际上是对法家株连无辜(连坐)思想的否定。从整体上看,“原心论罪”这一原则带有一定的人道倾向,是对当时酷吏暴虐司法的一种抑制。从董仲舒司法思想的价值取向看,他强调司法活动必须符合“仁道”(人道),应当以“泛爱群生”为基本目标;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应该明白“德生于和,威生于平”的道理,坚持“以中和理天下”的施政方针,注重司法公平、道德教化,从而实现“世治而民和”的理想社会。
供稿: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