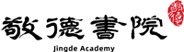李山: 中庸是什么
时间:2016-11-17
浏览:1518
值得注意的是,从“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开始,《中庸》的话题开始转为“天人合德”的亦宗教亦哲学的命题了。把“诚”命名为“天之道”是一个新说法。上天四季变化,周而复始,寒来暑往,云行雨施,从无差错,所以《中庸》就说“天”是一大“诚”道。“诚之”为“人之道”,是说,人从“率性之谓道”开始,不断努力,不断扩展自己的境地,最后应该像天地日月那样,无私无偏,包容负载,就是人生最高境界了。
供稿: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