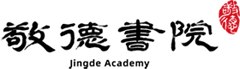敬德学刊
于闽梅:国学的品格和中小学国学教育的切入点
一、“国学的品格”
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国学的品格”。在某种意义上,国学就是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汉代以来,玄学标志着魏晋时代儒家对道家思想的吸纳,宋明理学则标示着儒家对域外佛教哲学的吸收。那么,今天,我们怎么进入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怎么引导学生学习中国哲学的品格?
国学的品格 , 其实就是当代新儒家代表之一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内在品格”(intrinsic character)。牟宗三先生在《儒家系统之性格》与《中国哲学之特殊性问题》这两篇文章中对此有较为详尽的阐释。
牟先生的学术背景是学习德国古典哲学的, 他的理论是想要把德国古典哲学跟儒家传统结合起来,这个尝试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实际上涉及到一种方法论,他想用我们当代人比较熟悉的逻辑学的方式来重新切入中国古代哲学,包括孔子、孟子,一直到朱熹和王阳明。但是他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那样,用西方的古希腊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哲学角度来讲儒家。我们现在有很多学者喜欢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这种方法是错误的。牟先生认为我们可以借鉴的是一种现代逻辑学的框架,用这个框架重新参照理解儒家。
用现代的框架来重新理解儒家,就有必要了解我们传统的框架。传统的框架实际上是一套纲目系统。什么叫纲目系统呢?比如说《文心雕龙》这样的古代文学理论著作,它的“纲”是《原道》篇, 当“道”作为纲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条目”来解释它,比如征圣、宗经。纲目系统的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当我们以“圣”为纲的时候,我们又会有很多相应的概念来解释它,在这个时候,《原道》篇又可以作为“条目”来解释“圣”。但是,我们现代人,甚至包括现代学者,对中国古代的这套纲目系统已经不熟悉,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是西方现代逻辑学的训练,所以要真正地“还原”古代的纲目系统是非常困难的。
牟先生提的这个比较有价值的观点,意义就在于他认为要去寻找中国哲学的原初真相、内在品格,寻找到儒学的内在品格。因为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与学生交流、与学者交流、与西方交流,必须要以现代逻辑学对国学进行重新梳理。
在牟宗三看来,中国哲学的品格跟西方哲学是不一样的,中国哲学确实有自己独立的品格。中国哲学是一个主体性哲学,就是“慎独”,这种慎独的主体性哲学涉及到一个个体如何通过修身,把自己变成主体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功夫在西方哲学是没有的,因为西方哲学是外向型的,是解决政治哲学内容为主的,不太注重主体的修为问题。牟宗三先生也强调,中国哲学的品格是一种主体构建的哲学。
回到“四书”,由于原来的纲目系统从现代逻辑学角度来说存在一些问题,我们读四书到底以哪一个为核心的时候,在中国古代哲学家那里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比如朱子对《大学》有自己的理解,到底什么是明德、止于至善,什么是至善?止于至善的这个至善究竟要落在什么地方,对这些问题不同的理解,导致朱熹和王阳明完全不同的讲法。朱熹讲儒家就是以《大学》为标准,致知格物、格物穷理。牟先生认为朱熹的问题在于他用《大学》做标准来决定《论语》《孟子》《中庸》和《易传》的基本走向,这样朱熹就稍微出了一点点偏差。王阳明则受孟子的影响,强调致知,强调“致知”就是“致良知”,牟先生认为王阳明这种讲法在文字学上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一种符合儒家精神的创见。所以王阳明拿《论语》《孟子》来规范《大学》,朱子是拿《大学》来规范《论语》《孟子》《中庸》和《易传》。那么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牟宗三先生说唐君毅先生的态度是对的,即当以《论语》《孟子》来规范《大学》,我们不能反过来用《大学》为标准来决定《论语》 《孟子》。因为从现代逻辑学的角度来说,《大学》本身的原意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范围内讨论的问题。
二、国学在中学、小学教育中的切入点
传统的蒙学教育是《三字经》《千字文》,朱子之所以会把《大学》《中庸》挑出来独立成篇, 跟《论语》《孟子》合在一起作为“四书”,补充原来的五经系统,就是考虑到经过蒙学教育以后的这个孩子,在真正的成长阶段要读什么书。“四书”是在宋代朱熹手中成型的。
这就是说,朱熹实际上考虑到当时的中小学教育的切入点,但是那个切入点放到今天来说,门槛太高了。因为朱子那个时代,甚至不要说朱子,就是鲁迅、胡适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刚开始改革语文教育,直接在中小学课本中加大白话文的篇幅, 其实并不是成功的。如胡适的学生唐德刚先生就曾说,对于我这样一个学生,我已经都会背四书的大部分篇章,《诗经》的大部分篇章,让我这样水平的人去读胡适的新诗,真的觉得反差非常强烈。因为他是从传统的蒙学开始进入四书系统,正好碰到当时民国的教育改革,胡适的新诗当时进入课本了,唐德刚说你让我这样会背《诗经》的人,如何去背胡适的新诗,如“小老鼠爬灯台”等这样的粗鄙的新诗?
我们现在反过来想这个问题,我们的中小学生,他们的起步恰恰是从类似于“小老鼠爬灯台” 这样的教育开始的。如果现在让他们直接进入“四书”,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非常痛苦的。这样我们就会遭遇到一个问题,在中小学的国学教育中,我们怎么样把繁复的内容变成简单一点的内容来传承我们的文明?这就涉及到我们怎么结合高考的教育,同时强化学生国学的教育。我们就是要把中小学教育看成一个种子,我们在培育种子,之后要让它健康地生发出来,所以要循序渐进,不能拔苗助长。
在中小学要做非常深入的纯哲学的国学教育, 在我看来很不切实际,因为我们首先在“小学”功夫,即古汉语基本的语法工夫上就不过关。我们今天的古汉语,相当于欧洲的拉丁文。欧洲人会拉丁文的非常少,欧洲中世纪以后的通行语言是拉丁文,当时的英语、法语、德语是地方语言。今天在欧洲,一个学生要是掌握拉丁文,难度相当于我们的学生来学习古汉语。所以我们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所谓的国学大师,连文法都不通,就是说都没有真正受过古代汉语的训练,怎么来讲国学?
古代汉语在我们的国学教育中非常重要,因为首先字词上不能出问题。我们目前的高考也在强化古代汉语的语法。在大学中文系,会进一步专门学王力先生那四册《古代汉语》。所以,我觉得中小学的国学教育,可以更侧重于文字的训练。在文字训练中老师举例子,可以从“四书”和《诗经》中来选文句,这样,就可以把“四书”的初级教育,包括《诗经》的教育,跟基本的语法训练结合起来。这样我们把种子藏在文法训练之中,学生到了大学,不管学什么专业,古典文化的训练已经类似于公民的素质教育,成为种子,无论学生以后学习什么专业,都会生根发芽。
五四运动的时候关于传统的国学教育要怎么进行,当时有两派观点。当然有很多人,尤其是我们现在网络上的西化派,非常喜欢举鲁迅的例子,说鲁迅曾经在回答记者提问,要给年轻人开一些书单的时候,鲁迅就说只读西方书, 不要读中国书。记者问他为什么,鲁迅说我看中国的书就想消沉,我看西方的书就想改造这个社会, 所以要让年轻人读西方的书。我们的网络习惯把鲁迅这种非常极端的观点拿来做片面化的理解。五四时代的那批学者,他们实际上面临着晚清以来持续的“中国问题”,即康有为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着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样的危机中,鲁迅的这句话更多的是针对小说而言的,就是说读中国的小说,比如读《红楼梦》《金瓶梅》这样的小说,会让人消沉,会想要做隐士,或者谈恋爱,或者遁入空门。但是读西方的小说,那些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就会想要改造这个社会。鲁迅就翻译了很多西方的,包括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鲁迅、胡适他们那一代的国学训练是非常深的,像鲁迅那篇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以看出他对魏晋文学的理解。他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也是去抄魏碑了。他的很多书,都可以看出传统的国学的训练是非常深的。
鲁迅的国学来源是什么呢?他的老师是章太炎,著名的经学家。整个晚清经学,经历了从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转向。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就是儒家的经学系统中两大分支中的一大分支——今文经学的代表。自从汉代在孔家古壁中发现了新的一批古文书以后,中国的儒家学派就分成了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两派的斗争一直延续到清代。清代康有为这一派重新复兴了淹没了将近一千年的今文经学,提出今文经学要变革,不要呆板地遵循孔子的思想,而是要进行变革。所以把鲁迅的传承弄清楚的话,就应该知道他是属于今文经学派,强调变革的那一派,这一派是非常激进的。鲁迅对于传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拿来主义”。他说一个年轻人从祖上继承了一个大宅子,你不能把东西都扔掉的,因为那里面有很多非常有用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要进行重新的分拣,要把好的留下来,这是鲁迅的拿来主义。
吴宓、钱穆先生则代表了另一派观点。他们提出我们整个教育必须要立足于国学的基础之上。钱穆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对比,就是今天的学者动不动就谈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说雅典是一个小城邦(应该还没有北京的二环大),而苏格拉底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雅典城,他的视野怎么可以跟孔子、孟子这样周游列国、有天下关怀的人相比?钱穆另外一个有名的对比就是,他把孔子、孟子到朱熹和王阳明比成了西方的耶稣到康德。他认为如果用基督教来做比喻的话,孔子和孟子相当于耶稣的地位,在中国哲学中,朱熹的地位相当于基督教的改革派,就马丁?路德开始的新教,新教出了最有名的哲学家康德。所以钱穆说,朱熹把魏晋南北朝新传过来的佛教,吸纳到儒家中,重新改革了儒家,一般新儒家这个概念是从朱熹开始讲起的。我们今天所说的海外新儒家,特意加了海外, 表明是儒家的又一次革新。新儒家就是从朱熹开始讲起的,那么朱熹跟马丁?路德,跟康德来对比, 钱穆说康德一辈子待在德国的小城里,而朱熹、王阳明他们是足迹遍天下的。所以钱穆说康德不能跟我们这样的大哲学家相提并论。钱穆立足在国学的基础上,他很反对崇洋媚外。
这是五四以来这两派的观点。哪怕像鲁迅这么激进的,他也是说我们对传统这个大宅子要进行“拿来主义”。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进行中小学国学教育的时候,不妨参照一下鲁迅以及钱穆先生的观点。
最后,国学的品格和中小学国学教育的切入点问题,涉及到的是我们怎么整合传统和现代的资源。王国维先生就说,我们中国国学的学术传统必须要不断的有源头活水来,比如说中国哲学从百家争鸣时代起,就进入了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跟其他几大文明(古希腊、希伯莱、印度)一起进入了高峰时代。但是,正如王国维所说,学术与思想的发展,要不断地吸纳新的资源,所以我们在魏晋南北朝, 玄学整合了儒家与道家思想。而在唐宋之际,我们把佛教哲学中国化了,这才产生了宋明的理学、心学。所以王国维说,由于历史上不断地有源头活水来,我们的思想发展越来越丰富。但是,王国维那个时代(晚清民国),他说我们本来碰到一次新的机会,即中国哲学去整合西方哲学的一个机会,但他认为他们这一代完不成这个任务。为什么呢?因为早期整合佛教的资源,是我们去东南亚取经,我们是非常开放地拥抱外来文化,热爱才能真正地吸收和整合。但是鸦片战争以来, 我们是被坚船厉炮打开了国门,王国维说晚清以来的学者是怀着羞辱心来面对西方资源的,整合不了这个资源,没有办法真正地去热爱。
王国维之后,牟宗三这样的学者就想要把西方的资源跟中国的资源进行进一步的整合。我很欣赏牟宗三先生的切入点,因为他本身比较了解德国哲学。他的切入点就是我们不要借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观点来看孔子,我们应该是把孔子放在一个非常主体性的位置,跟西方哲学来参照。
在这里我要回到开始提到的牟宗三先生的观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它是“主体哲学”,“不只是儒家重视主体,就是道家、佛家也同样重视主体,中国哲学与西方基督教不同就是这个地方”。主体哲学是以成全人为目标的。把握住这一根本区别,我们就能以非常清晰的内外有别的角度,来整合传统与现代资源,这一点,也即黄克剑先生所说的:在内(塑造主体)这一维度上,以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格教育为重心;在外(建立现代国家)这一维度上,以西方政治哲学为重心。只有进行如此内外有别地整合,我们才能真正地还原国学的品格,从而有效地把握住中小学教育乃至大学教育这一连贯的主体成长过程。
供稿: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