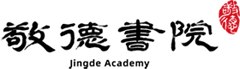庄亚琼 | 论中国古代“文明”话语的演进
随着文明理论研究的持续推进,近年多有学者讨论中西语境中“文明”一词的含义,以及古今中外文明观念的异同。然而,自“文明”一词于先秦典籍中出现,至近代以英文civilization为核心的西方“文明”话语传入,这中间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文明”一词的内涵是否有过发展变化?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话语折射出怎样的思想观念?中国古代“文明”话语演进的动力何在?以上问题尚有继续讨论的空间。话语是“‘作为过程的语言’,是动态的”,而任何一种话语的生成与变化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话语自身的文化传统是内因,激发话语运用的历史社会现实是外因。厘清中国古代“文明”话语的演进历程,有助于我们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连续性发展中把握中国古代“文明”话语的内涵,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文明观念,并为加速构建中国自主的文明研究体系提供更多的内生性学理支持。 一、中国古代“文明”一词的出处与原初含义 辨析中国古代“文明”话语的演变,首先需要追溯古籍中“文明”一词的出处与原初含义。 “文”与“明”早在汉字产生初期就已分别出现。就“文”字而言,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件扁壶上即存有朱书“文”。甲骨文中出现了更多不同形体的“文”字,其字形或如 先秦时期,“文”“明”多数情况下是作为独立的单音词分别使用,二字的连用分别出现在以下四类文本之中。 第一类是《尚书·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今文《尚书》无《舜典》篇题,除上述28字外的其他内容合于《尧典》。古今学界对此部分是否为伪曾有争议,现可基本认为其并非先秦内容。因此,虽然引据、阐释、化用《尚书》“文明”用法在后世十分常见,但在追溯“文明”一词的最早出处时,不宜过多依赖该条材料。 第二类是《礼记·乐记》:“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学界在《乐记》一篇的作者问题上有分歧,但基本可以认为它是先秦作品。其中的“文明”可宽泛解作“乐”之形态的显明、明白,是“文”“明”二字本义的主谓结合。 第三类是《周易·文言传》(以下简称《文言》)与《周易·彖传》(以下简称《彖》)。《文言》与《彖》上、下皆属《易传》,其中“《彖》的形成年代,不会早于孟子,可以定于战国中期以后,孟子和荀子之间”,《文言》的下限大致“当在《吕氏春秋》以前”。《文言》与《彖》中共出现六处“文明”:《文言》释《乾》卦(乾下乾上)二爻爻辞“‘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彖》释《同人》卦(离下乾上)卦辞“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彖》释《大有》卦(乾下离上)卦辞“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彖》释《贲》卦(离下艮上)卦辞“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彖》释《明夷》卦(离下坤上)卦辞“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彖》释《革》卦(离下兑上)卦辞:“‘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文言》中的“文明”是“文”“明”二字本义的直接组合。汉代王弼注其所在段为“与天时俱不息”,即以自然气候阐发乾卦二爻的性质;孔颖达认为:“‘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李鼎祚亦言:“阳气上达于地,故曰‘见龙在田’。百草萌牙孚甲,故曰‘文明’。”可见,《文言》之“文明”是描述万物于大地上生发,即以万物、百草等为大地之“文”,阳气之显见为“明”,具有蓬勃光明之喻。 《彖》中的五处“文明”用法更具系统性,是后世“文明”话语发展的源头所在。其具体内涵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文明非强犯的性质界定。文武并举的话语表述在周代已相当常见。《彖》从刚柔、文武的对应角度,解释《同人》《大有》卦象上离与乾的配合变化。王弼注为“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刚健不滞,文明不犯”,是后代学人从文武关系角度继续阐发“文明”语义的典型代表。“文明”一词也在与“威”“武”“刚”“犯”等具有强力、威暴特点的概念比较中,发展出强调和平、怀柔、非军事的话语内涵。其二,文明以化成的行为逻辑。《贲》卦本身象征纹饰。其中“人文”可直解为人类社会的样态,“化成”则具有鲜明的政治社会实践指向。可见《彖》在建立起“文明”“人文”“化成”三者相互关系的同时,也搭建了“文明”在政治和社会治理层面的话语空间。其三,文明为圣德的历史解释。《彖》在《明夷》《革》二卦中的“文明”表述并非纯粹说理,而是与解释圣王、圣贤的具体历史事件相结合。其中,以“内文明而外柔顺”解释周文王何以能够度过危难,以“文明以说”论述商汤代夏、武王伐纣的合理性。“文明”由此成为后世赞颂圣王圣贤之德的重要话语表述。 第四类“文”“明”连用的情况出现于《管子·侈靡》:“巨瘗堷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文明也……”房玄龄解该句为:“垄墓高美文明而不威也”,然而联系上下文意,颇有不通。郭沫若认为“文明”之前当脱一“使”字,并引用刘师培的看法,认为“明”当作“萌”,“‘文萌’谓画工雕工之类”,该句即意为使用雕画工匠。这一解释较为允当。 综上,除去可能的文字讹误,中国古代“文明”一词的原初含义可分为直接性与阐释性两个方面:直接性含义偏重“文”“明”二字本义的结合,如纹理显明或文辞鲜明;阐释性含义则聚焦圣王圣贤的美德与行为,与“和平”“怀柔”“人文”“化成”等概念互诠互释,具有政治和社会治理层面的话语指向。依托于《周易》丰富的诠释体系,“文明”一词逐渐有了超出“文”“明”二字本义简单叠加的多维度内涵,从而具备了发展为独立话语概念的基础。 二、“文德之明”:汉唐时期的“文明”话语实践 汉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话语发展逐步自觉的重要阶段。随着儒家经典在知识生活中尊崇地位的确立,蕴含了圣王圣贤之德及其统治逻辑的“文明”一词,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优势话语。 一方面,“文明”开始被广泛用于统治者与士大夫的褒谀美称之中。《后汉书》有“禹(邓禹)内文明,笃行淳备”“杜氏文明善政”之语;《晋成帝哀策文》言其“文明外润”;《续晋阳秋》评价晋简文帝“文明内融”;刘义恭赞南朝刘宋文帝“文明在躬”;谢朓称南齐明帝“文明固天启”;《文心雕龙·时序》并誉南朝齐的几位帝王“并文明自天”;北魏冯太后谥作“文明太皇太后”。另如“文明在中”“内镜文明”“允文文明”等丰富表述,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形容人之德行美好的重要话语表达。 另一方面,“文明非强犯”与“文明以化成”等政治观念被进一步明确。举例来说,西汉吾丘寿王《骠骑论功论》这样解释秦汉两朝同样运用武力却取得一乱一治两种不同效果的原因: (秦)既并海内之后,以威力为至道,以权诈为要术,遂非唐笑虞,绝灭旧章,防禁文学……是故皇天疾灭,更命大汉。反秦政,务在敦厚……天子文明,四夷向风。 在汉初“过秦”思潮的影响下,“文明”一词反威暴、重怀柔的基本含义,与儒家仁治、崇古、尊学等思想元素进一步融合。另如焦赣首次提出“文明之世”的表述,“文明之世,销锋铸耜,以道顺民,百王不易”,堪称中国古代农业社会视角下和平与发展的具体展开,反映了时人对政治和社会治理的基本认识。 汉唐时人普遍认为“礼”是“文明”在政治实践层面的具体内容。《文心雕龙·议对》:“自两汉文明,楷式昭备”,即将礼制的昌明完备视作“文明”。隋炀帝议定庙制时,褚亮奏言“当文明之运,定祖宗之礼”。唐德宗兴元元年自削“圣神文武”尊号,此后贞元五年、六年多有官员上表请复尊号。崔元翰之表文将“文明”与“先祖之典法”“烈祖之垂法”“累代之成规”等相等同,强调:“表朴而礼略,不如文明而化光”。可见,廓清礼制、彰明礼法即“文明”的应有之义。宋人李昉《历代宫殿名》载西晋已有“文明殿”,《玉海》载唐高祖于武德七年“宴王公亲属于文明殿”,五代时期,文明殿开始成为举行国家重大典礼的场所,这从侧面展现出“文明”话语在礼乐活动中的重要程度不断增强。后世诸如“姬公内则制礼作乐,以底文明之治”“圣世文明方讲礼”等表述,更点明了崇尚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文明”话语的基本内容之一。 在政治理论层面,“文明”一词开始出现在围绕祥瑞建构的政治叙事之中。自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理论,祥瑞便被视作君主有德、承天受命的证据。《晋中兴征祥说》:“王德盛则神鼎见。神鼎者,仁器也……世乱则藏于深山,文明则应运而至……成帝咸康八年,阳谷民刘珪夜见光,取得鼎一枚,外围四寸,此文明之应也。”以“王德盛”为“文明之应”的肇因,集中体现了祥瑞叙事对“文明”德性意义的利用。唐以降,涉及凤凰、麒麟、孔庙等同样被视为具有文德属性的祥瑞记载中,“文明”一词愈发多见。 实际上,“文德之明”正是汉唐“文明”话语的核心内涵所在。《南齐书·乐志》载有一篇食举歌辞: 王泽流,太平始。树灵祇,恭明祀。介景祚,膺嘉祉。礼有容,乐有仪。金石陈,干羽施。迈《武》《濩》,均《咸池》。歌《南风》,德永称。文明焕,颂声兴。 从其行文逻辑来看,“王泽流,太平始”是该篇的主旨,“树灵祇”至“歌《南风》”等礼乐活动皆可视作“王泽”“太平”的具体表现,“德永称”“文明焕”则是在呼应文首的同时总结上述现象。这里的“文明”一词不仅与具体的礼乐活动互为表里,也与“王泽”“太平”等儒家德治概念形成了彼此呼应的互诠关系。另如,《通典》载北齐武成帝时期宗庙乐舞之名:“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乐,为休德之舞。”《唐馀录》:“(后唐)懿祖室奏《昭德之舞》,献祖室奏《文明之舞》。”其中的“文明”亦与“休德”“昭德”相呼应,可见汉唐“文明”话语中显著的德性寓意。 总体而言,汉唐时期的“文明”话语以阐扬圣王圣贤之文德及其政治治理实践为主题。无论在“君子以文明为德”的个人道德层面,还是在“不修仁德合文明,天道如何拟力争”的政治观念层面,汉唐“文明”话语集中呈现了以德为核心的儒家政教观念。由于儒家典籍是汉唐之际知识文化活动所依凭的最重要的语料库,“文明”一词也相应具备了话语实践中的优势,因此产生了文明之世、文明之运、文明之应等话语创新。尤其是随着骈俪修辞的兴起与盛极,“文明”一词在对句中大量出现,在相对宽泛的文化语境下与“仁德”“太平”等其他具有德性意义的词汇发挥着相近的修辞作用,继而成为一种形容政通人和、安乐盛世的固定表达,并由此出现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场景之中。 三、“中国文明”:两宋时期的“文明”话语实践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明”话语发展演变最为关键的阶段。从外部环境看,在不同民族政权长期并立的政治现实下,“文明”一词被明确赋予了民族文化形态层面的话语功能。从内部思想看,随着理学的兴起,“文明”的话语重心逐渐转向尊崇儒学、倡明儒教,并开始被理学家用于论述中华文明历史的开端。 (一)“文明之兆”:政治合法性建构中的“文明”话语 纵观古籍中“文明”一词的使用频率,可以发现在宋代出现了一个陡然而增的趋势。造成如此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可能与宋尚火德、喜言火运有一定关系——八经卦中“离”象火,在时为夏,在位为南,《彖》以“文明”为“离”之德,是以在宋人论述火、夏、南方、赤色等概念时,往往会带出“文明”一词。另一方面,也是更为直接的原因,则在于宋人对本朝受命于“五星聚奎”的不断阐释。 五星聚合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受命符瑞,是指从地上观察水、金、火、木、土五大行星彼此距离不远地排成一线。北宋乾德五年三月出现了五星聚于奎宿的天文现象。王钦若作颂:“盖奎为鲁分之星,乃司文物……岂非运属文明,化符生育……此盖受命之殊贶也。”此后,以“五星聚奎”论证宋王朝应“文明之运”,可谓层出不穷。正是在这类阐发之中,“文明”与“太平”“仁德”等汉唐时期宽泛的、关注德性的修辞进一步区分开来。如南宋吕中认为: 五星聚奎,固太平之象,而实启文明之兆也。当是时,欧苏之文未盛,师鲁明复之经未出,安定湖学之说未行于西北,伊洛关中之学未盛于天下,而文治精华已露于立国之初矣。 不同于一般祥瑞叙事中将“文明”的德性显现寄托于模棱两可的自然现象,或真假难辨的神兽异物,这里对“文明之兆”的理解以“文”“经”“说”“学”等具体的文化与学术实践为准。宋理宗御赐濂溪书院匾额,刘元龙上表言“爰暨我宋,乃生周颐。以天挺贤哲之资,应奎聚文明之运”,则以理学大儒的降生为“文明”之应,集中体现了将文治、儒学之兴盛等同于“文明”的观念。 实际上,自欧阳修提出“正统论”并被广泛接受,宋代政治合法性建构中的神性元素就有所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治理权重的不断增加。以儒学昌明诠释“文明之兆”,并以此作为王朝正统性的依据,正是受到这一政治观念变化的直接影响。 明确以尊崇儒学为“文明”是宋代“文明”话语的一大突出特点,这与汉唐时期将广义的文化艺术活动的兴盛视作“文明”颇为不同。如李沆:“振复文明知圣作,尊崇儒术见天心。”夏竦:“三代既往,汉氏文明,专以儒臣表正邦宪,千岁之下,垂为旧章。”《金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期与万方同归文明之治,以为兴化致理,必本于尊师重道。”可见,儒学为“文明”话语的核心是当时社会的共识。 当然,宋代士人以崇儒为“文明”的基本内容,与其群体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通过强调宋朝“运属文明”的神圣性,士人群体也就能够合理放大其在政治文化层面的优势。所谓:“我朝以儒立国,故命宰相读书,用儒臣典狱,以文臣知州,卒成一代文明之治。”籍由搭建尊儒与“文明”的因果联系,士人群体的政治文化地位得以凸显、巩固。同时,在以儒学之兴为“文治之明”的观念影响下,统治者巡幸太学、祭祀孔子、广宣儒典等具体做法,即被等同于“文明”的实际举措。 (二)“华夏文明”:民族文化形态界定中的“文明”话语 中国古代“文明”话语发展至宋代的一大重要变化,即通过“文明”话语强化汉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一方面,在宋代重文的整体风气下,时人大多标榜自身以礼乐、文事为核心的文化形态。如晁说之多言“礼乐文明”,并以“尊孔氏,法诗书,躬仁义”为“振我国家礼乐文明之风”的具体举措。苏籀点明:“中国文明冠带之俗,士娴习于辞艺,不足者武也。” 另一方面,宋人开始将“文明”与“中国”“华夏”等概念连用。夏僎注《尚书·益稷》“帝光天之下”时引张载所言:“中国文明之地,故谓之光天之下。”朱熹解《尚书·舜典》“蛮夷猾夏”:“猾,乱。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国文明之地,故曰华夏,四时之夏疑亦取此义也。’”开始以“文明”为话语纽带将中国、华夏的政治地理属性与民族属性统一起来。 宋代“文明”一词的文化形态意义,突出体现在华夷之辩的语境之中。宋徽宗《宣和画谱》评述“日本国”画作:“蛮陬夷貊,非礼义之地……抑又见华夏之文明,有以渐被。”其中“华夏之文明”,既可以狭义理解为中国的绘画技艺与风格,也可视为华夏文化的泛称。再如,林之奇注《尚书·禹贡》“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揆文教者,揆中国之教也……此篇于绥服三百里谓之揆文教,其实奋其威武,守卫中国,不纯以中国文明之治也。 至于“中国文明之治”“中国之教”的具体解释,林之奇又言:“自绥服之外皆是夷狄之地,中国礼乐正朔之所不及。禹虽画为五服,其实外之,而不治之以中国之治也。”可见,“中国文明之治”所表述的正是以“礼乐正朔”为内容和特点的华夏文化形态。 “文明”一词之所以在宋代开始与“中国”“华夏”“礼乐”等概念连用,并发展出文化形态层面的话语意义,与赵宋政权面临的外部政治环境息息相关。如果说北宋士人还能超越华夷双方表面的文化样态,问出:“所谓夷者,岂被发衣皮之谓哉?所谓夏者,岂衣冠裳履之谓哉?”并认为只要能达到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治理,“德勉刑中,政修事举”,则“虽夷曰夏可也”。时至南宋,现实政治层面的困难使汉族士人普遍转向从文化形态(尤其是道德观念)上维持自身的心理优势。如朱熹以“德”“力”区分华夷:“中国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以德言之,则振三纲,明五常,正朝廷,励风俗。”其中“三纲”“五常”等皆是文化形态的具体体现。 以“文明”美称“中国”“华夏”是义理之学维护汉民族政权主体地位的话语手段之一。如尹起莘阐发朱熹《通鉴纲目》之所以直呼契丹国主耶律德光之名,乃“《春秋》贵华贱夷之法”,“中国,礼乐文明之地,不幸瓜分壤裂,莫能一统。若使酋虏亦例以国主称之,则是中国胥为夷矣。”其表述可谓南宋后期将“礼乐”之民族文化属性与“中国”之政治地理属性,统一于“文明”话语之中的典型体现。 (三)“鸿荒文明”:历史叙述中的“文明”话语 中国古代“文明”话语在宋代的另一重要发展,即开始以“文明”论述中华文明史的发端,从而正式赋予“文明”一词历史理论——尤其是历史发生学——层面的意义。 胡宏《皇王大纪》首篇即论:“鸿荒文明,天行也。鸿荒之世,结绳而治,理则昭然,其事不可详矣。”其中,“鸿荒之世”一词较早见于扬雄《法言》;《周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可见“鸿荒之世”与“上古之世”皆指人类发展的蒙昧阶段。胡宏将“鸿荒”与“文明”相对照,不仅赋予了两者自然时间维度上的先后关系,更赋予“文明”一词人类发展阶段的标识意义。此后学人所论“开辟至于今日,鸿荒化而文明”“上古风气未开,民淳事简,及其既开,人事迭变,日趋文明”等等,皆反映出“文明”一词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体系的重要话语组成部分。 具体来说,宋人多以伏羲作《易》为华夏先民走出蒙昧、步入“文明”的标志性事件。如王柏为车若水《宇宙纪略》作序:“天何言哉,感伏羲之心,假伏羲之手,开千万世文明之治。”而时人之所以将伏羲作《易》视作“文明”肇始,与宋代以道统为核心的古史谱系构建密切相关。所谓“既躬任于道统,宜上同于伏羲”,“道统”一词于唐代已出现,可理解为“道的传承谱系”。朱熹《大学章句序》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道统之祖。陈淳进一步阐发朱熹此意: 粤自羲皇作《易》,首辟浑沦,神农、黄帝相与继天立极,而宗统之传有自来矣。尧、舜、禹、汤、文、武更相授受……跻天下文明之治。 其中,“首辟浑沦”即中华民族摆脱混沌蒙昧、产生思想文化,也是“天下文明之治”的起点。从相对宽泛的文化语境看,所谓“皇乎三代,斯时已极文明;达在敷天,无往而非礼乐”,上古圣王圣贤对中华文明的开创、传承与发展,皆是历史叙述体系中“文明”兴起的具体内容。 总的来说,在宋代政治现实与理学观念的双重影响下,“文明”一词的话语内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拓展。无论是“文明之兆”所代表的政治合法性构建,“中国文明”所凸显的华夷文化形态差异,还是“鸿荒文明”所承载的历史叙述体系,皆具有“文治之明”的核心指向。宋代士人从自身的儒家文化立场出发,构建了与文治道统相结合的中华文明史框架,从话语上整合了儒家政治治理实践的内容与主体,折射出当时人对中华文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思考。 当然,也需要承认,在理学华夷观的影响下,宋代“文明”话语在很大程度上隐含了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优的文化立场。无论是以“文明”统纳礼乐名教,并以此进一步定义作为政治体的“中国”,还是以儒家道统的产生作为华夏先祖走出蒙昧、开启“文明之治”的标志,宋代“文明”话语都凸显了儒家政教观念的合法性与神圣性。 四、“文治之明”:元明与清前中期的“文明”话语实践 宋以降,学人进一步有针对性地阐发“文明”一词本身的政治理论内涵。如明代士人多将“文明”解作“文之极”,认为“文”有着远超文字、文章等直观含义的政治理论意义,是“古人道术教人行者也”,即儒家政教观念的载体。高攀龙强调“文明”一词的含义“非文词缋藻之工已也”,“记尧者曰文明,记舜者曰文明,则文明可思也。尧之文明曰亲九族,舜之文明曰徽五典,至德之圣,以天下让者在父子兄弟之间,则文明可思也”。其中“亲九族”“徽五典”皆是儒家“文治”观念的具体表达。汪应蛟言“唐虞之世,鸿荒始辟,然曰文思、文明,曰文德、文教,则文治固昭融矣。盖经天纬地,覆教明刑,修六府,和三事,圣人之所谓文也”,进一步点明“文明”一词是发扬儒家“文治”理念的话语载体。 (一)“大一统文明”: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文明”话语 元明清时期,不同民族政权交替入主,汉族与少数民族统治者皆注重运用“文明”话语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 明代士人常自诩其王朝当“大一统文明之运”,颂扬明帝王“逐胡元之昏君,除群雄之暴虐,大一统之基图,致文明之盛治”,“混一疆理,振古未有,文明声教,比隆唐虞”。但由于明代疆域面积虽强于南宋,却远无法与元朝比肩,且退居漠北的蒙古势力对明王朝仍有不小压力,是以明人多倾向于强调自身的正统性来自于对汉文化传统的恢复。诸如:“除腥羶之旧秽,布文明之新化”;“正中夏文明之统,复衣冠礼乐之旧”;“一洗中原夷虏之污,再阐华夏文明之治”;“欲除胡元左衽之俗,以复中国文明之治”等,可见其“大一统文明”代表的正是汉民族属性与儒家文化属性相绑定的政治身份定位。 当代学者认为明代“大一统”观采取的是“文治大一统”的思路,这一点在明代“文明”话语中也可见一斑。在政治治理的具体内容上,明代“文明”话语一方面继续推崇以儒学为核心的文教事业,“天启皇明大一统文明之治,开万载太平之业。在内则立胄监,在外则府州若县莫不有学,而学之教法规制,盖已超轶汉唐宋”。另一方面,关注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变荒裔之民为文明之俗”,则是明代“文明”话语在政治治理层面的重要拓展。有明一代,闽、琼、云、桂、粤等南部边疆地方志及赴任官员的往来文章中常见“文明之化”的表述,并以此为实现“文治之明”的具体举措。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明代部分“文明”表述对边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有所贬抑,但其实践逻辑之根基始终在于“华夷可变”。明人邹元标解《论语》“子欲居九夷而以何陋答”,强调“中国”与夷狄的差异只在地理区域,而非彼此之“真性”: 九夷不同者,地也。无王国无四裔皆同者,此真性也。同此父子,同此慈爱,同此夫妇,同此和睦,同此兄弟,同此友于,未见与中国异也。若欲以文明之习化之,是璞而琢之,丝而染之,擢其性也。 可见,华夷可变是“文明之化”能够实行的根本依据,而后者本身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中的重要话语表现。 实际上,围绕华夷议题展开的有关“文明”实践主体与实践方式的争论,正是明清“文明”话语演变的核心所在。 对明人而言,汉族统治与儒家“文治”皆是达成“文明”不可或缺的条件。明成祖朱棣致力于建立汉族皇帝主导的“华夷一统”,强调“君主华夷,覃霈恩泽,一视同仁,礼乐文明之化弘被远迩”。随着明中叶后内政外交压力的增加,部分明人论著中的“文明”表述开始重拾夷夏之防。如经历了“土木堡之变”的丘濬强调:“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为盛德,殊不知德在华夏文明之地,而与彼之荒落不毛之区无预焉。”这类着力凸显“文明”的汉民族属性的表述,甚至逐渐延伸至具体地域在历史上的归属界定。万历《顺天府志》追溯其地方历史:“然自石敬瑭割地以遗辽,文明之墟,染于腥秽。”可见,明代“文明”话语极力强调汉族政权的正统性。 相较而言,清朝统治者则致力于重新界定达成“文明”的标准,以此应对汉族士人“夷狄”不得为“正统”的攻讦。清雍正帝《大义觉迷录》中共出现19处“文明”表述,其语义语境几乎囊括了此前出现过的所有“文明”话语类型——既有与上古蒙昧相对应的文明开化,也有论述“文明”之祥瑞,还包括宽泛褒美王朝治下的太平盛世。其中,雍正帝对何为“文明之治”的阐发,集中展现了清代“文明”话语对“华夷之辨”的突破: 不问为何代之衣冠,皆足以为文明之治……岂以衣冠之相似,而遂可以文明不坠,礼乐不废,不至于乱乎?……即此可见衣冠之无关于礼乐文明、治乱也。且如故明之末年,衣冠犹是明之衣冠也,而君臣失德,纲纪废弛,寇盗蜂起,生民涂炭。区区衣冠之制,礼乐文明何在也?可能救明代之沦覆乎? 其中“衣冠之制”指向政权的民族属性。雍正帝反对将“衣冠”之俗与“文明之治”相等同,其根本目标在于有针对性地消解宋、明“文明”话语对汉族政权正统性的强调,从而为其统治合法性辩护。曾静《归仁说》将清朝统治者与“蔑视诸夏礼乐文明之治”的夷狄相区分,明确将是否发扬儒家政教与学术作为“文明”与否的标准。可以说,清前中期的“文明”话语,正是其“一统无外”政治观念的集中体现。 (二)“文明之盛”:历史理论研究中的“文明”话语 宋以降,以“文明”与“鸿荒”(或洪荒、鸿濛、洪濛、混沌)相对应的历史叙事,逐渐成为学人追溯上古三代时的固定表达。元人胡一桂《史纂通要纲断》继续将上古圣王置于“鸿荒—文明”的演进过程中统一讨论:“盘古生于太荒……诚开辟之圣人,而启天下后世以无疆之治,享文明之盛者,皆其创始效也……伏羲、神农二圣人去洪荒之世未远也,其风犹为朴略。至黄帝之世,实为文明之渐。”其中“文明之渐”的提法,已反映出进一步细致阐述“文明”演进历程的历史意识。王心敬以伏羲为“肇开文明之圣”,周公为“立千古文明之宗范”;王夫之通过划分“文明初起”至“文明已盛”的历史阶段性变化,解释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必然性;冯琦认为“一代之气正如四时”,其中“开创之初”为春,“物力既盛,文明日侈”为夏,“文明既洩,物力亦诎,盛极而衰”为秋,“上下萧条,公私贫匮”为冬。上述引征皆反映了历史理论讨论中“文明”话语的逐渐丰富。 实际上,追溯“鸿荒”与“文明”的最早对应,已可发现其中蕴含着事物从混沌到有序、从粗粝到精备的发展逻辑。因此,与前者含义有交集的榛芜、荒陋、草昧、朴略、狉榛等词,在明清时期也逐渐与“文明”组成对照表述,用以描述具体事物——尤其是具有人文属性的具体事物——从初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人文发展程度较高状态的“文明”并非线性进化论中的高级阶段。如果说“鸿荒—文明”对应的是人类历史发展大循环的开始,在此大循环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治乱兴衰则又构成了一个个小循环,也就是所谓的“自羲黄以降,草昧文明,市朝屡改”。在这类循环史观的语境下,“文明”往往也与“浑厚”对应,两者共同构成一种以“文”“质”转化为内核的历史发展观。如明人魏校多有“浑厚开文明”之论:“天地气化,初极浑厚,开盛则文明,久之渐以浇薄,盛极则有衰也。”王樵《祭祖乐章》亦言:“兴衰之效,于古有征。恒由浑厚,以开文明。文明既开,浑厚渐失。谓偶可常,至于骄佚。”可见,明人通过阐发“文明”与“浑厚”所具之不同价值及相互关系,理解治乱兴衰,并为崇俭戒奢、去繁就简的政治理念提供思想支撑。 明中后期,社会危机不断加剧,秉持经世思想的学人开始深入运用“文明”话语阐发其历史盛衰观。举例来说,历史“气运说”认为,人类历史运动变化的实质是“气”的盛衰复始,“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人世间的治乱也随着气运之变循环往复。对于其中隐含的历史宿命论色彩,部分学人颇有批驳。王立道对“尧当一元文明之会”的讨论即为其中的典型。 “一元文明之会”语出熊禾,因被录入《五经大全》流传甚广。其中的“元”“会”,皆为邵雍提出的时间单位;一元内有十二会,其中以地支比十二之数,则一元之中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之所以说尧“当一元文明之会”,是因为尧处于“午之会”,“得天地之中数”,因此才有古今所不及之盛世。对此观点,王立道不以为然。他并不否认“人事”与“气化”二者对治乱与否皆有影响,但认为“人事”之作用当较“气化”在先: 人事既尽,则虽气化之衰不能使之乱,人事既失,则虽气化之盛亦不能使之治耶……吾是以知文明之会意者,天之不能违尧,而非尧之必有得乎天也。 随后,他又列举了尧当政之时“治洪水”“播五谷”“敷五教”等“人事”活动在促成“治世”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强调“文明”的政治治理内涵,“尽人事而后可以言天”,反对附着在气运论之上的历史宿命论观点,这集中体现了经世史学观念与“文明”话语的结合。 总体而言,在“华夷”“大一统”等元明清时期核心政治议题上,如何看待实现“文明”的主体与方式问题,成为不同历史时期统治阶层的共性关注。明代相关“文明”话语有着较为明显的民族辨判与文化识别的考量,清代统治者则着重从政治和社会治理的实际成效角度界定“文明”的概念。与此同时,“文明”一词开始被广泛用于指代人文生活发展程度较高的状态,并蕴含一定的“文”“质”交替的非线性发展观内涵,成为历史发展动力、历史盛衰论等深度历史理论问题的重要话语组成部分。 余 论 中国古代“文明”话语的产生,源于先秦人民对美好德行与政治治理问题的深刻阐释。自汉代开始,中国古代“文明”话语逐渐融入儒家政教实践,形成了“文德之明”“中国文明”“文治之明”等话语主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学术“内圣外王”之旨归。可以说,理解中国古代“文明”话语的关键就在于理解“文明”的实践主体、方式与目标。 中国古代“文明”话语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中国知识文化传统的连续性。“汉字具有单字词独有的意义存储优势……要求阅读者必须将浓缩于字词中的丰富意义尽量释放出来。”不断阐释、转化运用经典文献中的字词是中国古代知识体系连续性发展的关键一环,中国古代“文明”话语也是在这一经典阐释学传统中发展起来的。自《易传》出现“文明”一词始,其语义发展呈现出丰富化、意向化的整体趋势。举例来说,汉代王弼从天时、天气理解《周易·文言》“天下文明”,此时的“文明”仍主要是纹理鲜明的直接性含义;唐人孔颖达在此基础上添加了“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意在凸显其光彩灿烂的寓意;宋代大儒程颐将“天下文明”解为“龙德见于地上,则天下是其文明之化也”,强调了“文明”语义中化成的行为逻辑;明人汪应蛟论乾坤有大生之道:“以太极为一本,以亿兆为同气,蛮夷戎狄皆吾同室,鸟兽草木皆吾并生……《易》之‘见龙’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仲尼所自谓也。然天下已文明矣。”其对“天下文明”的运用则进一步表达了超越华夷、物我一体的话语指向。中国古代“文明”话语的“生长”演变,正是其作为知识资源不断被转化、拓展的过程。恰如刘家和先生曾指出的:“中国古代文明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既表现在语言文字方面,也表现在学术传统方面。”中国古人对《周易》《尚书》等始源性经典文献的连续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是中国古代“文明”话语得以形成的最重要内源性因素。 中国古代“文明”话语逐渐丰富的外在条件则缘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演变。“话语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言语表达。”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如何论证自身从天受命、继承正统是历代政权构建自身合法性的关键所在。从汉至宋,统治合法性的思想建构多以五德终始、谶纬等学说为基础,尤为重视构建以“德”为核心的话语体系。而对文德的具体理解,则既可以落脚在某种祥瑞,也可以与反威暴、倡仁义、兴礼乐等相对宽泛的政治主张相联系,是以这一阶段的“文明”话语也相对宽泛(在部分情况下,广义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发达都可被视作“文明”)。随着欧阳修正统论的提出及理学的兴起,以“大一统”作为政治合法性所在的思想转变,使宋以降的“文明”释义逐渐锚定于儒家政教实践的落实,即“文治之明”。在此过程中,承载文治的政治体(中国或华夏)、文治的具体内容(儒学、儒术)以及文治的实行者(信奉儒家文化的统治者与儒生)共同明确了“文明”的语义边界。至此,“文明”不仅正式具备了文化形态层面的内涵,更成为兼具中国古代“道统”与“政统”双重意义的话语符号。不同于西方近代“文明”话语依据种族、地域与文化形态等建构了“文明”与“野蛮”之间严格的等级壁垒,中国古代“文明”话语虽然在部分历史时期存在以汉文化为优的倾向,但从整体上看,华夷可变始终是其在政治和社会治理中的逻辑内核。明清时期,汉族与非汉族的统治者皆通过调整“文明”话语在民族属性与治理方式上的侧重,展现自身的政治合法性,生动展示了中国古代“文明”话语与政治实践的相互作用。 进入近代后,欧洲在对外扩张过程中所建构的、具有欧洲中心论特点的“文明”话语深刻改变了中文“文明”的固有内涵。然而,即便是在欧洲文明观念及其话语空前强势的近代,部分中国学人对中国古代“文明”话语在未来可能发挥的功用仍抱有乐观态度。晚清学者吴汝纶为日人根本通明所著《周易象义辨正》作序:“《易》之书,天下之公书,非一国所得而私焉者也。且如欧美诸国,今皆称为‘文明’。‘文明’云者,《易》家言也。浸假欧美学者并能读《易》,谓《易》所称‘文明’为欧美发也,吾羲文之《易》,不又远行于欧美矣乎!”其中令人动容的不仅是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广阔胸怀,更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自信。 世异时移,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本质要求之一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代持续推进,人们对中国文明观念何以由来的探索兴趣日益浓厚。他们可能也会如百年来尝试从西文civilization理解欧美文明观的中国人一般,籍由中国古代“文明”话语体悟中国文化传统与历史智慧——这种可能,正是我们持续发掘以“文明”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话语资源的必要性所在。 来源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微信 (《后》2.14.13),或中部增有其他条纹形状,如
(《后》2.14.13),或中部增有其他条纹形状,如 (《甲》3940)、
(《甲》3940)、 (《乙》6821反)等。徐中舒将“文”释为“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纹饰,故以文身之纹为文”,并归纳了“文”字的三种用法,分别是:“文,美也。冠于王名之上以为美称”,“人名”,“地名”。《周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段玉裁注“错当作逪”,认为“逪画”——即交错的纹理——是“文”的本义。在此基础上,“文”字逐渐引申出修饰、文字、文章等含义。就“明”字而言,《甲骨文编》收录24例“明”字,如
(《乙》6821反)等。徐中舒将“文”释为“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纹饰,故以文身之纹为文”,并归纳了“文”字的三种用法,分别是:“文,美也。冠于王名之上以为美称”,“人名”,“地名”。《周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段玉裁注“错当作逪”,认为“逪画”——即交错的纹理——是“文”的本义。在此基础上,“文”字逐渐引申出修饰、文字、文章等含义。就“明”字而言,《甲骨文编》收录24例“明”字,如 (《前》4.10.4)、
(《前》4.10.4)、 (《乙》6150)等。从其日月并列的字形可见,“明”字的本义是日月光之明亮,引申为明白、明显、公开等含义。
(《乙》6150)等。从其日月并列的字形可见,“明”字的本义是日月光之明亮,引申为明白、明显、公开等含义。
供稿: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