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武:大气、正气与家国天下
作者:吴国武(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敬德书院学术委员) 浩气:至大至刚 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其中的“大”是非常重要的。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指出:“言气,则先大。大,气之体也。”“气”跟“大”谁最先,他认为是大在气先,如果气不够大,气就不是他认为的气,所以他说“大,气之体也。”解决我们“小里小气”问题,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按照程颐的说法,那小里小气的“气”其实就不是什么心志道义之气。真正的气,“大”是它的根本特征。所以,孟子自己就讲要“先立乎其大”。大不是空的东西,就是你自身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如果有一个你不认识的人需要帮助,你能去帮助,这就是你的“不忍”,一点都不空。大家可以发现,《孟子》书里讲“大”的地方特别多,孟子特别喜欢讲“大”,共讲了103次,“小”讲了53次,讲“小”大部分都是针对于“大”的反面来讲的。其中,讲“大人”讲了12次,讲“小人”讲了16次,小人都是从反面来讲的,对应的还是大人。《孟子》书里还常会出现“大丈夫”“小丈夫”“贱丈夫”这些词,从中就可以发现孟子对“大”的重视,这就是我前面讲的“气之大”。 《孟子·滕文公下》里面有一段话,其实这段话对我们今天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这段话讲战国时期有很多飞黄腾达的人,特别是那些纵横家,天天游说君王,得到荣华富贵,且权高位重。景春就是一位纵横家,他曾经问孟子:“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公孙衍和张仪都是当时最有名的纵横家,我们知道在《史记》里面有《苏秦张仪列传》,苏秦张仪都是纵横家的代表人物。公孙衍、张仪这两个人当时游说君王,都得到了权臣的位置而名满天下。所以景春就反问孟子,公孙衍跟张仪两个人难道不是大丈夫吗?他们“一怒而诸侯惧”,他们不高兴了,就动员君王灭掉哪个国家;或者“安居而天下熄”,即他们如果不想使天下大乱,就能够让战事停息,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大丈夫吗?孟子回答说了一段话,他说: “是焉得为大丈夫乎? 子未学礼乎?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是焉得为大丈夫乎?”意思是这样的人难道叫大丈夫吗?然后他就说你有没有学过礼仪?“丈夫之冠也,父命之”,也就是说父亲来主持加冠成人之礼的仪式,你才能够成为“丈夫”。从中你发现孟子是怎么反驳的,是从“丈夫”的本义来讲起的。然后他说“女之嫁也,母命之”,就是说女孩子出嫁的时候是由母亲来训导嘱咐的。母亲告诫女儿说,到了你丈夫的家里,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毕敬必戒,无违夫子”就是夫妇和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即以和顺、顺从为做人原则的,那是妾妇之道。由此他特别讲“大丈夫”应该如何?逢迎君王和有独立人格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说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等等后面一大段话。大家回过头来想,我前面所提到的“此之谓大丈夫”,就知道为什么孟子讲这番话?他是批评当时用不正当手段得到权位、为所欲为的那些人,而且批评很厉害,这里面就反映了孟子所谓“养气”的一些思想,就是对于这个大丈夫之“大”是有很多考虑的。 还有《孟子·告子上》第十五章里面所提到的观点,也值得我们去仔细阅读和思考的。比如说,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公都子是孟子弟子,他问老师,同样都是人,为什么有些人是大人,有些人是小人,这是怎么回事?我想很多同学也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人是大人,有人是小人,孟子解释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大气”,就是说你要是自己小里小气,那你肯定是个小人,即使你现在没表现出自己是小人,将来也会表现自己是小人。你如果是“从其大体”,你知道你的气、你的浩然之气是你自身固有的,你还能够把它充塞于天地之间,那你肯定是个“大人”,即使你现在还没有表现出来,将来也会表现出来。公都子继续问:“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同样是人,为什么有些人只满足次要感官需要,有些人却能满足身心大体?孟子就讲:“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指除了心这个器官以外,你的其他感官都是跟着外物走的。“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就是它们都是跟着外物走,只有你的内心,它是能思考通贯的,而你的耳朵和眼睛却不能。我们今天知道,从生理学上讲人的神经系统的协调才能够使你贯通,包括理性思考在内。古人认为只有你的心才能思考通贯。“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于我者”,这也是孟子经常讲人禽之别里面讲到的,耳朵、眼睛、嘴巴动物都有,它们唯一没有的是什么?是不忍人之心、仁义之心。因此,这才是你最重要的,要先立乎其大,那是老天爷给予人类最宝贵的东西。所以,人跟一般的动物不一样,就在于老天爷给予我们的心。如果先立乎其大的话,就是你的仁义之心要先立起来,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立天地之心”,“则其小者弗能夺也”,也就是说好听的、好看的、好玩的,各种东西都能够听你的心来指挥。“此为大人而已矣”,意思是大家想成为大人很容易,就看你心里想不想,你心里想,心想事成是肯定的。 (正)气:以直养 关于正气,“以直养”的正气,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孟子·尽心上》里面经常讲到修身养性的问题,孟子说:“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按照我们今天的讲法就是先身正,你自己身正了,你才能够正外物。这是大人的一个特点。朱熹解释浩然之气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正气的问题,气要得其正而不能是邪的。比如,文天祥的《正气歌》,对我们民族精神影响是深远的。过去读《正气歌》的时候,你可能不能完全理解何谓“天地有正气”,我今天给大家讲了孟子思想以后,大家就知道了文天祥思想的来源是孟子。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行。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佩乎塞沧溟。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天地之间,天上你可以看到日月星辰,地下可以看到山川河流。“于人曰浩然,沛乎塞沧溟”,也就是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意思是国家处于清明太平时期,朝廷祥和开明。“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意思是国家在艰难危急的时期,正义之士能表现出气节,让高尚的情操名垂青史。孟子在我们的精神传统里经常是在忧患时期、在讲究气节的时候往往就不断重现,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传统中非常核心的一些要素。它在平常时候不一定能够凸现,但是在关键时刻,我们民族精神中最核心的品格就会显现。这是我对孟子的一个理解。 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浩然之气,用梁启超先生的话来总结。我觉得梁启超先生对中西之变、古今之变过程中如何创造性转化传统思想,对我们有很多启发。古代人讲“学以至于圣人之道”,在梁先生一本有关儒家哲学的书里,他把“圣人”转化为了“人格健全的人”。梁先生还有一处讲到对孟子的理解的时候,用“自强”来解释孟子。我想这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他说: 浩气者,人性中阳刚发扬之法也。人类之所以能向上,恒恃此,缺焉则馁,馁则无复自信力,而堕落随之矣。此气本人性所同具,曷为或强或弱,或有或无,则以有害之者,害之奈何,为其所不为,欲其所不欲,日受良心之责备,则虽欲不馁焉不得也。气之为物,易衰而易竭者也,馁而再振,其难倍蓰焉。养之之法,惟在自强,自强则能制伏小体,不为物引(老子曰“自胜之为强”)。而不慊于心之行可免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尽心》上)。“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公孙丑》上《不动心》章)。 “浩气者,人性中阳刚发扬之法也。”我们前面讲了浩然之气又大且正,这是所谓“阳刚发扬之法”。“人类之所以能向上,恒恃此,缺焉则馁,馁则无复自信力,而堕落随之矣。”如果缺少阳刚发扬之法就会没有自信力。“此气本人性所同具”,我觉得这一点他讲得非常对,而且对孟子的理解也很对,孟子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孟子非常具有现代性。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这就是具有特别现代性的话,不是只有某一个王公贵族能够成为尧舜,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尧舜。“曷为或强或弱,或有或无,则以有害之者,害之奈何,为其所不为,欲其所不欲”,浩气为什么在每个人身上有强有弱,时有时无,取决于你们有没有真正地做该做的事情,想该想的事。所以他说“日受良心之责备,则虽欲不馁焉不得也”,所以你固有的浩气想不变小都不可能。“气之为物”,我们知道气球打满了气以后它慢慢地也会消掉,所以它本身是易衰而易竭的,需要你不停地存养。所谓的“馁而再振”,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振奋精神。“养之之法,惟在自强”,晚清至民国初年正是国家遭难的时候,所以梁启超先生特别强调自强,他用“浩然之气”来作为自强之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他后面基本上都是引孟子的话来讲,特别讲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说的是抬头望天、低头看人,不能够亏欠于天地,不能够愧对他人,这些都是孟子的原话。“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是他对浩然之气的新理解,我觉得这些地方对于我们来讲,应该能够得到很多启发。我们对浩然之气,对养气自身的渊源有一个了解,同时对于我们如何来养气也有新的推动,我们不是就养气来谈养气,而是我们要从国家民族的自信自强这些方面来讲养气的一些内涵。 (本文来源于秦红岭主编、林青副主编《建筑与人文:名家通识十一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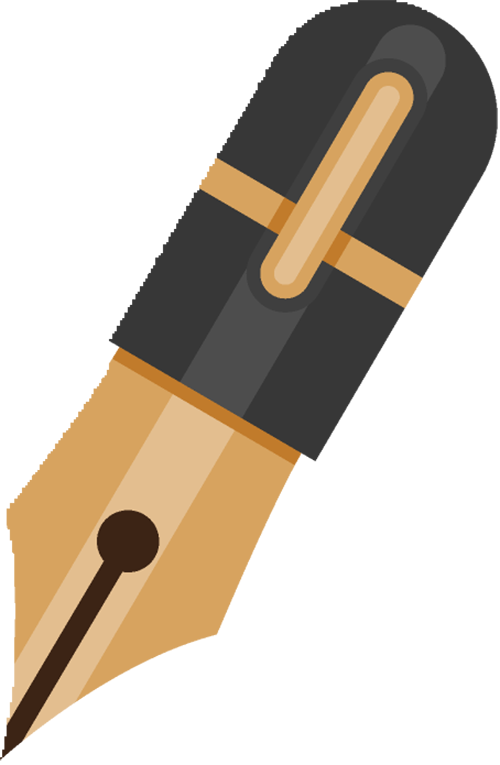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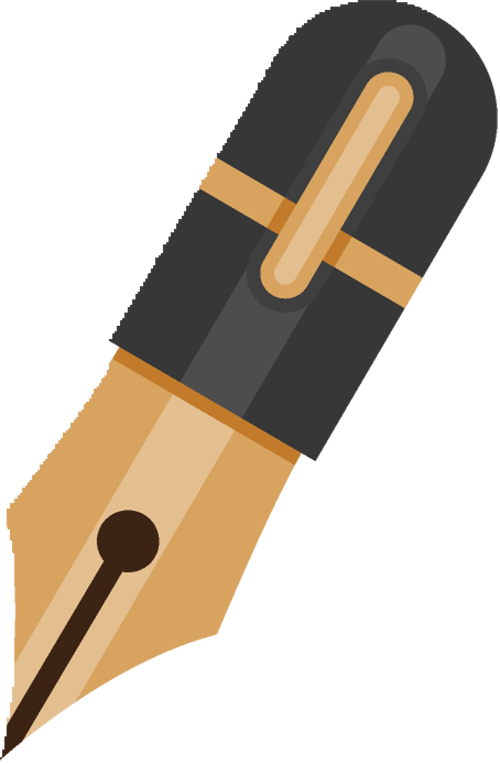
供稿:敬德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