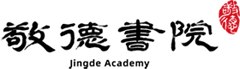陈乔见 | 朱熹的圣经解释学(上)
摘要:朱熹的解经学认为圣经(圣人之言)体现着融贯一致的天地之理,这是解经得以可能与必要的先验条件,也表明解经的目的是通过圣人之言把握天地之理。就具体方法而言,朱熹一方面充分吸收汉唐注疏的训诂成果,但也认识到注疏学之陋,不足以理解圣人之意和天地之理;另一方面他与其他宋代学者一样强调义理之学,但却也十分警惕宋人好为高论新说的空疏之敝。一方面主张随文(经)解义,另一方面也强调理会意味,切己体验。虽说追求圣人原意和圣经本意是朱熹解经的首要目标,但他也认为有的解释未必是圣经本旨,却也是一极有价值之解释,因为它揭示了某种道理。虽说朱熹具有强烈的圣经贤传意识,但他也认为对于以往错误的解释不应当人情回护,而应辩其是非曲直。在不疑与有疑、训诂与义理、原意与发明、善意原则与人性原则之间,朱熹总是保持着某种张力与平衡,使得解释成为一项既有规范亦不乏创造的意义活动。
关键词:朱熹 解释 圣经 圣人之心 天地之理 作者陈乔见,中山大学哲学系暨东西哲学与文明互鉴研究中心教授。
一、引言
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宣称:实用主义是各种理论的公共走廊。[1]仿其言,吾人可以说:诠释学是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的公共走廊。诠释学(德文Hermeneutik,英文hermeneutics,又译解释学、阐释学、释义学等)在西方发展颇为成熟,洪汉鼎先生如此概括:“综观西方诠释学的发展,我们一般可以区分两种诠释学:一是以方法论为主要取向的诠释学理论或解释理论(Interpretationslehre),其代表人物有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以及以后的埃米尼奥·贝蒂和汉斯·伦克(Hans Lenk)等;一是以存有论为主要取向的诠释学哲学,其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以及其后试图批判和综合哲学诠释学的哈贝马斯、利科和阿佩尔等。”[2]两种基本的诠释学也就是学界常说的方法论诠释学和本体论诠释学(或哲学诠释学)。潘德荣先生指出,目前“诠释学”仍无一个统一的定义,何为诠释学的问题只能通过考察诠释学史来具体回答。不过,他也给出了一个关于诠释学的一般性界定:“诠释学是关于理解与解释的理论,而所有的理解与解释都是指向‘意义’的。就此而言,‘意义’乃诠释学的核心概念,追寻‘意义’的理解是诠释学理论各种体系的共同出发点。” [3]由此出发,展开了诠释学研究的三个向度:一曰“探求作者之原意”,如施莱尔马赫的一般诠释学、狄尔泰体验诠释学;二曰“分析文本的意义”,如贝蒂和利科尔,他们认为文本具有某种客观意义,且不再由作者的主观意向所规定;三曰“强调读者所悟(接受)之义”,这便是伽达默尔所开启的哲学诠释学。[4]潘先生认为方法论诠释学在西方是大宗,我国诠释学研究过多关注伽达默尔一脉的本体论诠释学,这有点类似于“别子为宗”[5]。
受西方诠释学的影响,21世纪初,汤一介先生撰写了系列论文讨论“创建中国解释学”,并对中国古代解释经验做了一些理论概括。[6]毋庸讳言,尽管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传统,也不乏有关经典解释的经验总结或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但像近代西方那样以“诠释学”为名的专论几乎没有出现过。这其实也不足为怪,近代西方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等人之所以能够创建学科意义上的诠释学,实有其历史渊缘。前者是为了反对浪漫派的主观主义和怀疑论,后者是为了回应并仿效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而思考和提出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两者都受到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转向的深刻影响。反观中国经学史、哲学史或思想史,似乎并不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认识论转向,故反映在解经学或诠释学领域中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反思自然外缘不足。因此,关注创建或重建中国诠释学的学者无不认为,创建中国诠释学最为首要的任务是总结、反思和提炼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过程中的种种原则、规则、方法或预设等,诚如张江先生指出:“核心和要害是,中国学术传统中,虽无阐释之学的概念和学科,但有丰富的阐释学思想和经验。这是构建当代中国阐释之学的可靠资源和坚实基础。在学科化问题上,我们当然要学习借鉴西方阐释学成果,但不是用西方阐释学的已有框架来裁剪或规制中国阐释学经验和思想。”[7]这确实是创建或重构中国诠释学或阐释学的当然之则和必由之路。
本文即在此问题意识下,尝试重述在中国经学史和哲学史上具有丰富的经典解释经验和方法论反思意识的朱熹“圣经解释学”。实际上,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在创建或重构中国诠释学的过程中,朱熹受到的关注最多。对西方诠释学颇有研究的潘德荣先生便很早就对朱熹的诠释思想有所重构,他说:“在中国经学史上,朱熹是第一个相对集中地谈论过阅读和诠释的方法论的学者。‘理’是他的哲学体系的本体论概念,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经文原义、圣贤原意与读者所悟之意是理解过程中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理解的目标就是这三种意义的整体圆融和谐之‘理’。语言解释与心法理解是其诠释的基本方法。”[8]不难发现,潘先生在朱熹的诠释学中找到了与西方诠释学相对应的三个向度。就解释经验的反思讨论而言,朱熹的《读书法》勉强算得上是最具诠释学意识的作品。陈立胜先生即根据朱熹《读书法》来讨论其诠释学的意蕴,他重点考察了朱熹的“圣贤意识”“读书心态”“读书次第”等,其结论是:“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朱子读书法之精髓,则非‘敬’字莫属……这个‘敬’字折射出其阅读共同体乃是一信仰共同体,在此信仰共同体所隶属的生活世界中,经典乃是神圣的文本(圣经),其神圣性正是读者(信仰者、修行者)在其相应的信仰生活、阅读过程中得到接受的。朱子的读书法实际上揭示了儒学信仰共同体在阅读其圣经过程中所具有的种种性格,这与时下盛行的‘合法成见’、‘作者死了’、否定原意之类的当代西方诠释学确实存在着许多扞格不入的地方。”[9]陈先生认为朱熹的读书法与伽达默尔强调的“合法成见”、利科强调文本独立于作者的当代西方诠释学扞格不入。不难发现,潘、陈二人对朱熹诠释学的理解视角并不完全一致。尽管朱熹的诠释学或解释学颇受关注,形成了不少研究文献,研究者各自视域和目的不同,各具特色。[10]但是,笔者以为仍有一些重要的思想未被注意,下面笔者将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重述朱熹的“圣经解释学”,为了相对全貌地反映朱熹的解释学思想,难免重复前贤已经表达过的部分内容和观点。
二、“圣经解释学”释义
我首先根据朱熹自己的术语,将其对儒家经典的解释经验的二阶反思命名为“圣经解释学”或简称为“解经学”。理由如下:其一,关于“圣经”。今人看到“圣经”二字便联想到犹太教和基督宗教的Holy Bible,这确属数典忘祖。其实,至迟在汉代五经立为官学以后,儒家已经形成了“圣经贤传”的文本及其解释系统,张华《博物志·文籍考》:“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在经历了魏晋到隋唐时佛教的兴盛之后,面对“儒门淡泊,皆归释氏”的境遇,宋儒的圣人、圣经、圣学意识尤为强烈。朱熹便经常使用“圣经”一词,兹仅举两例,其《大学章句序》云:“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11]其《读书法》云:“如解说圣经,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己,全然虚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12]那么,其所谓的圣经主要是哪些呢?朱熹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自书契以来,《二典》、《三谟》、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谓尽矣。只就文字间求之,句句皆是。”(14,345)又说:“《六经》《语》《孟》皆圣贤遗书,皆当读,但初学且须知缓急。《大学》《语》《孟》最是圣贤为人切要处。”(14,412)又说:“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17,3450)简言之,朱熹所谓圣经主要指“六经”和“四书”,又认为“四书”是“六经”之阶梯,故他更为重视“四书”。如所周知,朱熹倚重“四书”并为之章句集注,建构了一套理学体系,自此“四书”的地位实际上取代了汉唐“五经”的地位,圣经文本的转变也表征着解经学范式的转移。
其二,关于“解释”。尽管儒家圣经解释体例众多,常见的如传、记、注、义疏等,朱熹多用“解释”或“解经”一词括之,试举几例如下:
解经谓之解者,只要解释出来。将圣贤之语解开了,庶易读。(14,351) 《礼记》乃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之书。(17,2888) 自晋以来,解经者却改变得不同,如王弼、郭象辈是也。汉儒解经,依经演绎。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16,2245) 后世之解经者有三:一、儒者之经;一、文人之经,东坡、陈少南辈是也;一、禅者之经,张子韶辈是也。(14,351—352) 凡先儒解经,虽未知道,然其尽一生之力,纵未说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17,2767)
不难看出,朱熹用“解释”或“解经”来涵括历代传、记、注、疏和同时代人的解经形式或作品。
其三,关于“学”字。今人一看到“某某学”之“学”字,总是联想到以“-logy”为后缀的英文单词,其实西文Hermeneutik或hermeneutics并不如此,若在对解释经验的方法论反思或其他二阶反思的意义上而言“学”,朱熹等传统儒家当然自有其解释学。进而,儒家所谓“学”不仅有认识论或方法论的意义,而且也有实践的意义。朱熹的圣经解释学强调义理之学,义理一方面指文本的义理,一方面也指应当付诸实践的当然之理。
综上,根据名从其主的原则,笔者以为将朱熹有关儒家经典解释经验的二阶反思命名为“圣经解释学”是比较合适的。本文不是在西方某一诠释学理论视域下对朱熹解经学的重构,而是顺着朱熹解经学自身的脉络做一重述,下面笔者将从朱熹解经学的根本目的、解经形式、解经方法和原则等方面分而述之。
三、因圣人之言求圣人之意,因圣人之意求天地之理
朱熹认为解经的根本目的在于探求圣人之意或圣人之心。朱熹《〈论语集注〉序说》后附《读〈论语〉〈孟子〉法》引程子曰:“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13]如前提及,西方方法论诠释学有两种,一种是强调探求作者原意,一种强调探求本文原意。就此而言,这段论述表明读书解经探求的是作者(圣人)原意。当然,圣人之意只能凭借语言文字而求得,故探求圣人之意自然离不开探求本文原意,如朱熹说,“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14]便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知道,庄子认为圣人之意(道)不可言传,“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随后庄子便用“轮扁斫轮”的例子说明圣人之意(或道)不可言传,圣人之言不过是圣人之道之糟粕耳。与此不同,朱熹坚信圣人之意就体现在圣人之言中,是可以言传的,其《〈论语〉要义目录序》云:“圣人之意,其可以言传者具于是矣,不可以言传者,亦岂外乎是哉!”(24,3614)朱熹相信,“圣经贤传所以告人者,已竭尽而无余”(18,3796),故可“察言以求其心”(24,3625)。圣贤之意不多不少就体现在圣人之言中。这里关乎文(言)与道的关系,针对汪尚书“语及苏学,以为世人读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于此求道”的看法,朱熹明确主张文以载道、求道于文的观念,“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21,1305)。总之,道不离文,因文而可求意,即文而可求道,这是朱熹解经学的基本预设——这与庄子“意(道)不可以言传”和禅宗所谓“佛法妙理,非关文字”的观念绝异。
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探求圣人之意的最终目的是探求天地之理。朱熹说:“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天下之理。”(18,3805)“《六经》是三代以上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又说:“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14,347、314、345)朱熹所谓天下之理、天地之理、自然之理,其义一也,都指公共的道理,它包含“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如所周知,朱熹认为“性即理也”,众人与圣人一样,心中本具天地之理,但由于众人受到气质之拘、物欲之蔽等,“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15],圣人便是这样的聪明睿智之先知先觉者,众人理解并依据圣人之言做工夫而复其性之本体,从而成为有德之人。这也便是朱熹经学的实践意义。
四、圣经若主人,解者犹奴仆
朱熹的“圣经”意识要求把“圣经”视为主人而把解经者视为奴仆。朱熹说:“圣经字若个主人,解者犹若奴仆。”(14,351)经的解释应该围绕并服务于经,“经之有解,所以通经。经既通,自无事于解,借经以通乎理耳”(14,350)。解之于经,只具有工具的意义。在儒家圣经解释史上,曾出现过所谓“宁道孔圣误,讳闻郑服非”(《旧唐书·元行冲传》)的地步,汉代经学家郑玄、服虔的地位竟然超过了孔圣的地位。在朱熹看来,这是不可接受的,尽管他认为东汉诸儒解经煞好,但总体上汉代人训诂章句并未能很好地理解圣贤之意。朱熹《大学章句序》:“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16]把汉唐注疏斥为俗儒记诵词章之学,并与佛老异端虚无寂灭之教相提并论,贬斥之意十分明显。《宋史·道学传》云:“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与。”认为儒家圣经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至北宋周、张、二程等出方焕然而大明,也表达了同样对汉魏两晋唐人注疏之学的贬斥。实际上,“故先儒谓圣经不亡于秦火,而坏于汉儒”(17,2897),这是宋儒共识,而这也标志着解经范式的转变。用清儒“汉学”“宋学”的区分来说,汉学重训诂,较征实;宋学重义理,较精微。但是,这一常见的化约也容易遮蔽一些问题,比如朱熹就十分重视训诂,他只是反对把汉人诂经文字看得比圣经本身更重要。
在解经形式上,朱熹的圣经意识指引他反对“舍经而自作文”:“汉儒解经,依经演绎;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16,2245)在此方面,朱熹遵循汉儒成规,“盖平日解经最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说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长也。”(21,1349)确实,既然注疏等是用来解释经义的,那么解经文字就不能喧宾夺主。朱熹《记解经》云:“凡解释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则注与经各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经。”(24,3581)“盖解经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释得文义通,则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间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一片道理,经意却蹉过了。”(17,3422)
在解经的实质观念上,朱熹的圣经圣学意识反对挪用异教的思想观念来附会儒家经典。许顺之来书问:“‘空空如也’,或者多引真空义为问,如何?”朱熹答曰:“理会正当文义,道理自在里许。只管谈玄说妙,却恐流入诐淫邪遁里去。”(22,1739)“空空如也”典出《论语·子罕》:“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时人有用佛学真空义解释此句,朱熹认为只需正当如实理解文义,若以佛解儒则会流于邪道。朱熹经常批评两苏之学与王安石之学,也在于此,“至于王氏、苏氏,则皆以佛老为圣人,既不纯乎儒者之学矣,而王氏支离穿凿,尤无义味”,苏氏之言,“语道学则迷大本(朱熹自注:如前注中性命诸说多出私意,杂佛老而言之)”(21,1300)。王、苏之学,皆杂引佛老解释儒学,这只会丧失儒学根本。朱熹批评陆象山杂禅为学界公案,且看他一段议论:“某尝谓,人要学禅时,不如分明去学他禅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圣贤之言夹杂了说,都不成个物事。道是龙,又无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静旧年也不如此,后来弄得直恁地差异!”(17,3437)杂禅解儒,则儒学成四不像,必将丧失儒家之真精神。程允夫谓“程氏于佛老之言,皆阳抑而阴用之”,朱熹答曰:“夫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程氏之学以诚为宗,今乃阴窃异端之说而公排之以盖其迹,不亦盗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则所谓诚者安在?……若儒者论道而以是为心,则亦非真尊《六经》者。”(22,1863)人或疑二程夫子亦杂佛解儒,阳儒阴释,朱熹为之辨正澄清,以为二程之学以诚为宗,必不如此,若阴窃佛氏观念以入儒家而又公然排挤之,那无异于作伪,亦非真正尊奉“六经”。
总而言之,朱熹认为“道在《六经》,何必它求”(21,1299),“异学决不可与圣学同年而语也”(21,1293)。确实,我们在朱熹解经作品《四书章句集注》中,找不到佛、道二家的特有观念。至于朱熹受到佛氏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佛氏的思维方式回应佛氏之挑战,比如黄宗羲批评朱熹的“离气言理”“离气言性”仍是佛氏“逃空堕幻之见”,[17]实与朱熹所谓杂佛解儒者不同,因为在朱熹看来,无论是“理”之名(概念)还是“理”之实(仁义礼智),无不是正统儒家观念。
朱熹解经学中的圣人圣经意识,实际上蕴含了当代分析传统中与翻译和解释有关的“善意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或译“厚道原则”“宽容原则”等)。善意原则最早由威尔逊(Neil L. Wilson)于1959年提出,其后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等皆有论述。戴维森认为善意原则是解释理论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使解释成为可能的东西”[18]。在《真理与意义》一文中他如此说明:
在解释他人词语和思想中的善意(charity)在另一个维度上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们必须最大化一致(maximize agreement),否则将有使外族人谈论内容无意义的风险一样;我们必须最大化归于外族人的自身一致性(self-consistency),否则便不能理解他。[19]
戴维森在此强调了两层意思:其一,解释者应追求他与被解释者之间在信念上的最大化一致;其二,解释者应该设想说话者认为真的大部分句子是真的。[20]大致地说,“善意原则无非是让人尽可能把被解释的语言材料往好的方面想,比如尽可能设想它们是真的,不矛盾的,有理性的,等等”[21]。不难发现,朱熹的圣人圣经意识,认为圣人之言和圣人之心就体现了天地之理,认为儒家圣经的义理具有一致性,解经者应尽可能通过阅读和解释圣经而获得吾人本具的天地之理,以便与圣贤保持一致,以及其所谓经如主人而解者如奴仆、“有疑者,却要无疑”(14,343)等说法,无不体现着善意原则。诚如戴维森所言,“善意原则”是使得解释和理解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同理,如果朱熹不把其解释对象视为蕴含着天地之理的圣经,那么他的解释与理解活动便没有可能。
来源:孔学堂杂志社公众号
供稿: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