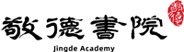孟子“道性善”的内在理路及其思想意义
孟子“道性善”是当时思想界的一件大事,而如何理解孟子“性善论”也是当今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孟子“性善论”已成为了一个谜。要解开这一个谜,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以西释中”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回到孟子去,“以孟释孟”,从孟子的内在理路、思维方式去理解孟子自己,庶几才能找到答案。
一、孟子以前的论性方式及孟子对“善”“性”的独特理解
孟子“道性善”,其直接的现实关怀是“距杨、墨”,确立儒学的价值理想;从思想的发展来看,则是对他以前论性方式及人性观点的超越。人们之所以对孟子“性善论”产生种种误解,往往也是因为将孟子“道性善”与其以前的论性方式混同起来。故在讨论孟子“性善论”前,先要了解孟子以前论性的方式与特点。据《孟子·告子上》: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注:舜同父异母弟),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公都子在这里列举了孟子以前三种不同的人性主张,分别是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说,无名氏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说,以及同为无名氏的“有性善,有性不善”说。可以看到,这三种人性论有一共同特点,即它们都是将“性”看作为一客观对象、事实,根据性的种种具体表现,对其作经验性的描述、概括,类似一种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由于观察、分析的角度不同,其具体结论也有所不同。告子由于着眼于性的具体内容,认为“食色,性也”,而“食色”本身无所谓善与不善,关键在于外界的引导,故认为“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东西也”(同上)。第二种人性论关注于环境与人性的关系,注意到当文王、武王这样的贤君出现,社会得到治理时,百姓往往乐于为善;当幽王、厉王这样的暴君出现,社会陷入混乱时,百姓则往往变得残暴。故认为人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关键在于环境的影响。第三种人性论则注意到,人性之善恶似乎并不完全是由外因所决定的,如,有尧这样的贤明君主,却有象这样坏的百姓;有瞽叟这样坏的父亲,却有舜这样好的儿子;有纣这样邪恶的侄儿,且为君主,却有微子启、王子比干这样的贤臣。所以,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有些人性善,有些人性不善。以上三种人性主张,虽然具体观点有所不同,但其论性方式则是相同的,其中有些观点也是可以协调、相通的,例如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说,若着眼于“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同于“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
对于以上的言性方式,孟子并不一概反对,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懒);凶岁,子弟多暴。”即是承认人性之善恶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孟子亦承认,对于一般民众来说,“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梁惠王上》)认为物质财产对于一般民众的道德水准,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但以上言性方式,只是对性的一种外在概括和描述,不足以突出人的道德主体性,无法确立人生的信念和目标,不能给人以精神的方向和指导,更不能安顿生命,满足人的终极关怀。故孟子言性,不采取以上的进路,而是另辟蹊径,提出了他对“善”与“性”的独特理解。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告子上》)
公都子前面既问人性的问题,则孟子“乃若其情”的“其”,也当是指人性而言,但它不是指一般的人性,而应是指下文的“才”,也就是“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或仁、义、礼、智。“乃若其情”的“情”应训为“实”,指实情。下面“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两句中,分别出现两个“善”字,但具体所指又有所不同。其中前一个“善”是就具体的善行而言,如“见孺子将入于井”,必生“怵惕恻隐之心”,而援之以手;见长者必生“恭敬之心”,为其“折枝”等等;后一个“善”是就人性自身而言,是对“其”也就是对性所作的判断和说明。这三句话是说,至于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的实情,可以表现为具体的善行,这就是所说的善。所以孟子实际是即心言性,认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可以表现为具体的善行,所以是善的,并进一步由心善肯定性善。这里,“其”既是指“性”也是指“心”,而孟子都称其为“才”。对于善,孟子还有一个定义: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尽心下》)
“可欲”也就是可欲求、可求,是孟子特有的概念,所以要了解什么是“可欲之谓善”,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可欲”。对此,孟子有明确的说明: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之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之在外者也。”(《尽心上》)
孟子在这里区分了两种“求”:“求之在我者”与“求之在外者”。前者是可以由我控制、决定的,得与不得,完全取决于我,所以是可求的;后者则不是可以由我控制、掌握的,得与不得,要受到“道”和“命”的限制,所以是不可求的。那么具体讲,什么是“可求”、什么又是“不可求”的呢?孟子对此亦有说明: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
孟子认为,“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乐音声,鼻之喜芬香”(赵岐注),四肢贪图安佚,这些声色欲望及其对世俗富贵显达的追求,能否实现,要受到外在条件的限制,故君子将其看作是“命”,而不是“性”;而仁义礼智这些内在的德性,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自己,故君子将其看作是“性”,而不是“命”。显然,在孟子看来,声色欲望、富贵显达是不可欲、不可求的,而内在道德禀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可欲、可求的。故“可欲之谓善”实际是说,不受外在条件的限制,能充分体现人的意志自由,完全可以由我欲求、控制、掌握的即是善。这种“善”当然只存在于道德实践的领域,具体讲,也就是人生而所具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或仁义礼智是善。
由此可见,孟子以上对“善”的两个定义是密切相关的,“可欲之谓善”是就内在的禀赋而言,是说内在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或仁义礼智是“可欲”“可求”的,因而是善的。“乃若其情,可以为善,乃所谓善也”则是就功能、作用言,是说内在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能够表现出具体的善行,就是所谓的善。但是孟子只强调“可以”,认为只要“可以为善”,就算是善;假如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表现出善,仍不影响内在禀赋本身仍为善。这里,“可以”是“能”的意思,表示一种能力。[1]所以,“可欲之谓善”是对善的本质规定,对于孟子而言,善首先是指“可欲”、“可求”,也就是不受任何外在条件的限制,完全可以由我控制、掌握,能真正体现人的意志自由,实际就是对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或仁义礼智内在道德禀赋的欲求。恰如康德所言,只有对善的意志才可以无任何限制而被称为善,孟子亦认为,只有对仁义礼智的欲求才可以无任何限制而被称为善。“乃若其情,可以为善,乃所谓善也”则是对善的补充性规定,是说“可欲”“可求”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可以为善”,能够表现出具体的善行,就是善。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只是“可以为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故孟子实际是以内在道德品质、道德禀赋为善,这种道德禀赋即是“才”,即是“心”。“心”可以表现为具体的善行,因而是善。
孟子对善的这种理解,较之于前人显然是一种发展与创造。孟子以前,“善”作为一个名词,往往是指善人、善事、善行等,而善人、善事、善行之所以被称为“善”,乃是因为其符合社会、民众的一般认识,所以如果将善定义为“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的话,那么,它显然反映的是社会、习俗的外在标准。孟子之前人们谈论性善性恶,也是以这种外在标准为标准,凡符合这一标准者即为善,与这一标准相反者即为不善。《孟子》书中虽然也保留了善的这种用法,但孟子“道性善”却不是指这种意义的善,而是以内在的道德品质、道德禀赋为善,此道德品质、道德禀赋可以表现为具体的善行,因而是善,所以反映的是主体自主、自觉的内在标准,孟子的善可定义为:己之道德禀赋及己与他人适当关系的实现。
孟子不仅对“善”的理解与前人有所不同,对“性”的看法也有不一致之处。孟子之前,人们往往是把性看做一客观的对象与事实,孟子则不然。前引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表明孟子亦承认“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事实上也是一种性,但又认为君子并不将其看作是性。这里前一个“性也”,是一个事实判断;后面的“不谓性也”,则是一个价值判断。孟子又认为,仁义礼智的实现,虽然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命的限制,但“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里的“不谓命也”,同样是一种价值判断。所以如学者所指出的,孟子论性“最大的特色即在于摆脱经验、实然的观点,不再顺自然生活种种机能、欲望来识取‘人性’。他从人具体、真实的生命活动着眼,指出贯穿这一切生命活动背后的,实际上存在著一种不为生理本能限制的道德意识——‘心’,并就‘心’之自觉自主的践仁行义,来肯定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性’所在”。[2]在孟子看来,人生而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此四心作为一种内在的道德禀赋与品质,“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可欲”“可求”的,同时可以由内而外表现为具体的善行,因而是善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虽非人性之全部,但它们是人之异于禽兽者,是人之“真性”所在,人当以此为性,人之为人就在于充分扩充、实现此善性。所以孟子性善论实际是以善为性论,孟子性善论的核心并不在于性为什么是善的——因为“把善看作是性”与“性是善的”,二者是同义反复,实际是一致的,而在于为什么要把善看作是性?以及人是否有善性存在?
二、善性之证成:形上预设与“示例”
关于人有善性,孟子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首先是承继了“天命之谓性”的传统,将善性溯源于形上、超越的层面,认为是天的赋予。前引《告子上》孟子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即是认为仁义礼智不是通过学习、实践从外部获得的,而是本来即有的。本来即有,实际也就是上天赋予的,故孟子又引《诗》予以说明:
《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告子上》)
对于孟子所引《大雅·烝民》,徐复观先生曾分析说,“在周初用彝字,多指‘常法’而言,有同于春秋时代之所谓礼。‘秉彝’,是守常法,《毛传》以‘执持常道’释之,有如所谓‘守礼’……而上文之‘有物有则’,指有一事,即有一事之法则,‘民之秉彝’,即民之执持各事之法则。并未尝含有性善之意。”[3]但孟子既引用此《诗》作为性善之证,自然就不应从《诗》的原意去理解,而应从孟子的引用意去理解,按照孟子的理解,“秉彝”显然是就人性本身而言。以上四句是说,天降生众民,赋予其善性,有一事必有一事之法则;民既然秉持其善性,必喜好这美德。故在孟子看来,善性是来自天,是天的赋予。
孟子又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同上)“心之官”即心之器官,是就心的经验层面而言,“得之”则是得心所具有的仁义,而此仁义即是“天之所与我者”。由于仁义来自于形上、超越的天,故能不受感性欲望、生理机能的限制与束缚,“思则得之”,“求则得之”,是“可欲”“可求”的,因而是善的。所以,对于孟子而言,由于人皆有“天之所与我者”,因而也皆有善性。不过,天赋予人善性或“此天之所与我者”乃是一个超越的命题,而不是知识的命题;其所反映的是理性的事实,而不是经验的事实。而孟子论性,虽然不限于感性层、实然层,同时也上升至超越的当然层,但并不是将其分为两截,而是看作连续性存有之整体。故孟子在溯源于天,肯定善有形上、超越的源头之后,又强调人有善性亦有着事实的根据,可以在经验世界中得到显现与证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
以上文字常常被学者看作是孟子对性善的证明,此乃大误。人性善乃是对人性的全称判断,是说人性的全部内容及表现都是善,而这显然是不能靠有限的举例来证明的,若要举人性可以为善之例来证明性善,同样也可以举人性可以为不善之例来证明性恶,这样的举例可以是无限的,故对于证明性善实际没有任何意义。其实,孟子以上论述只是要证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就是人皆有善性,而人皆有善性与人性是善虽有联系,但所指显然是不同的。人皆有善性是说人性中皆有善的品质和禀赋,皆有为善的能力,但不排除人性中还有其他的内容,所以即使为不善,也不能否认善性的存在。人皆有善性当然也不可以通过有限的举例来证明,但由于它近乎一种事实,实际上是任何人都难以否认的,故孟子举出“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这一特殊事例,以说明人确有本心、良心或善性的存在。大凡一个人的善行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发自于内,是本心、良心的呈现;二是来自于外,是为了达到某种世俗、现实的目的。前者是真正的善,由这种具体的善行可以反推它一定有内在的根源、根据,也就是善性存在;后者虽符合一般人们对善的理解,即“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但道德力量却大打折扣,不属于孟子所理解的善。而孟子上文所说的“怵悌恻隐之心”,是在“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也就是在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预期的心理状态下突然发生的,它显然是发自于内,而不是来自于外;是发自“不忍人之心”、内在善性,而不是出于外在世俗目的,不是为了讨好孩子的父母,不是为了邀取乡党的美誉,也不是讨厌孩子的哭哭啼啼。所以,从“怵悌恻隐之心”的显露,最足以说明人确有“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内在善性的存在。而孟子举出此例,其用意在于使每个人都可以置身其中,设身处地,反省到自己亦必生“怵惕恻隐之心”,并援之以手,更进一步反省到自己以往的生活中亦有过众多类似的经历,从而洞见到内在善性的存在。的确,任何人在其生活中都会有本心、良心的呈现,这恐怕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既然否定不了,那就应该承认,人确实皆有善性存在。孟子只需要通过一“启发性的示例”,将此点明、显现出来即可,故孟子上文所举,乃是一项“示例”,而不是一个例证。面对这一“示例”,假如有人认为自己确实从没有产生过同情心、羞恶心、是非心、恭敬心,那么孟子的回答是,“非人也”,认为他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了,故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除了上文外,孟子还讲了“古人葬其亲”的故事,同样是“示例”。
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蔂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滕文公上》)
这一故事不必有事实的根据,其目的在于通过这一“示例”,说明羞恶之心也就是善性的存在。上古尝有不葬其亲者,后看到被自己抛弃的亲人尸体,在沟壑中被狐狸吃,蚊蝇叮,头上不由冒出冷汗,侧过头去,不敢正视。头上的冷汗,不是流给别人看的,而是“中心达于面目”,是内在的羞恶之心在面容上的显现。面对这一“示例”,每个人都会发觉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从而确信人皆有善性存在。
人之善性可以在特殊情景中呈现、流露,于此可以说明善性的存在,但在孟子看来,最能体现人的价值与尊严,最能反映人之特殊性的,莫过于人可以为了价值理想,为了善而牺牲自我。故“生死关头的抉择”“生死关头的醒悟”,也是孟子说明人皆有善性的重要“示例”。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生命是每个人所渴求的,死亡是每个人所厌恶的,但是在生死交关的一刻,为什么会有人挺身而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不正足以说明,人性中还有比自然本能、生理欲望更高的要求,也就是对仁义礼智的要求,所以抵死也要维护人性的理想与尊严。而且“舍生取义”,“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无丧耳。”即便一个穷困潦倒的路人,即将倒毙的乞丐,如果对其没有起码的尊重,“嘑尔而与之”,“蹴尔而与之”,则“行道之人弗受”,“乞人不屑也。”(《告子上》)可见,羞恶之心以及对尊严的渴求,是人皆有之,只是保存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这除了说明“仁义礼智”,“我固有之”外,恐怕再找不到其他合适的理由了。
所以,孟子一方面从形上的层面预设了善性的存在,认为“此天之所与我者”;另一方面又强调,“此天之所与我”的善性是可以在经验世界具体呈现的。形上的预设保证了善性的普遍性,经验世界的呈现则证明了善性的真实性,二者相结合,说明了人皆有善性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故孟子“此天之所与我者”或天赋予人善性虽是一个超越的命题,但并不是没有事实的根据,并不是不可以在经验世界得到检验与证明。一些研究孟子的学者,往往只强调孟子“性”超越、先验的一面,认为孟子将性由“感性层、实然层,上升至超越的当然层”;孟子把性看作“一项不受个别经验否证,却必须承担所有道德生活、价值经验的意义解释的形上概念”。这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自觉不自觉将西方的两层存有论带入孟子思想中,而孟子言性的最大特色,便是不将形上、形下,先天、经验,超越、内在分为两截,而是彻上彻下,一体贯通。这尤其体现在他对于“四心”“四德”及其“才”的理解上。
三、性善之成立:理由、根据及意义
孟子肯定了人皆有善性后,进一步需要说明,人为什么要把善性看作是真正的性。对此,孟子又从“人禽之辨”“性命之分”“大体小体之别”三个方面做了论证。先看“人禽之辨”: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
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尽心上》)
张岱年先生分析说:“孟子亦尝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则孟子以为人之与禽兽,所异者不若所同者之多,是孟子并不否认人有不善的性质即与禽兽相同的性质。又谓‘无教,则近于禽兽’,便更可以见了。然则何以仍讲性善?此由于孟子所谓性者,实有其特殊意谓。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徵。人之所同于禽兽者,不可谓人之性;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实即是人之‘特性’。而任何一物之性,亦即该物所以为该物者。所以孟子讲性,最注重物类之不同。”[4]徐复观先生亦说:“孟子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与一般禽兽,在渴饮饥食等一般的生理刺激反应上,都是相同的;只在一点点(几希)的地方与禽兽不同。这是意味着要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只能从这一点点上去加以把握。……孟子不是从人身的一切本能而言性善,而只是从异于禽兽的几希处言性善。几希是生而即有的,所以可称之为性;几希即是仁义之端,本来是善的,所以可称之为性善。因此,孟子所说的性善之性的范围,比一般所说的性的范围要小。”[5]在现实生活中,谁都不愿被骂为畜牲,不愿意与禽兽为伍,这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人还有不同于、高于禽兽的特性,这些特性才能真正显示出人之不同于禽兽之所在,显现出人之为人的价值与尊严。所以,如果不是把“性”看作是对生命活动、生理现象的客观描述,而是看作一个凸显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确立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概念,那么,当然就应该以人之不同于禽兽的特性,也就是仁义礼智为性,而不应以人与禽兽都具有的自然本能、生理欲望为性。
再说“性命之分”。这方面,孟子继承了前人的天人之分思想,并做了进一步发展,从外在限定与内在自由的角度论证了人当以善性为性,而不应以生理欲望及对富贵显达的欲求为性。竹简《穷达以时》的出土,帮我们了解到孟子以前的“天人之分”思想:“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第1—2简)竹简认为,关系世间穷达的,不仅有人而且有天,天人各有其分。天人之分就是说天人各有其职分、作用、范围,二者互不相同。在竹简看来,穷达祸福取决于时运,是“可遇而不可求”,非人力所能控制、掌握的,这些都属于天不属于人;而一个人的德行如何则取决于自己,与天无关,所以积极行善,完善德行才是人的职分所在,才是人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明白了这种“天人之分”,就不应汲汲于现实的际遇,而应“敦于反己”,只关心属于自己职分的德行,“尽人事以待天命”。孟子受到这种天人之分思想的影响,并将其发展为性命之分。孟子认为,“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这些感官欲望与仁义礼智虽然都属于性,但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仁义礼智内在于性,由于人有意志自由,“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能否得到完全在于自己,与命运无关,所以是“在我者也”;而感官欲望以及对富贵显达的追求等虽然也出于性,但“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能否实现取决于命,所以是“在外者也”。仁义礼智体现了人的意志自由,不受外在条件的限制,所以应看作是“性”;感官欲望、求名求利,能否实现不是由我控制、掌握,所以只能看作是“命”。不难看出,孟子的“性命之分”实际就是来自竹简的天人之分,是对后者的进一步发展。[6]而孟子通过这种“性命之分”,也就是内在自由与外在限定的区分,说明人当以仁义礼智也就是善性为性,而不应以感官欲望为性。
还有“大体小体之别”。孟子弟子公都子曾问: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的人成为有德的大人,有的人成为无德的小人?孟子认为,这是因为人有“大体”、“小体”的区别,“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并分析了为什么有人会从其大体,有人会从其小体: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告子上》)
小体指“耳目之官”,大体则指“心”,二者具有不同的性质与作用。耳目之官不能“思”,也就是不具有自主性,只能以外物的作用为作用,故当其与外物接触时,便会受到遮蔽与引诱。心之官则不同,它可以“思”,此“思”为反思、为逆觉体证,故心之官一方面会受到外物的干扰、引诱,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思”,反求诸己,发现“天之所与我”的仁义礼智,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因此,只要首先将心中的仁义确立起来,耳目之欲才不会扰乱、夺取它,这样便成为有德的大人君子。既然“大体”“心之官”能“思”,具有自主性,其仁义来自天的赋予,反映了人的内在本质;“小体”“耳目之官”不能“思”,不具有自主性,其耳目之欲来自外物的作用,不能反映人的自由意志,那么,自然应当将心之官所具有的仁义也就是善性看作是性,而不应将耳目之官所产生的耳目之欲看作是性。
所以,孟子以善为性,虽然是一种价值选择、价值判断,但并非没有事实为依据,并非没有充分的理由与根据。孟子以善为性,也并非只是出于自我论证的需要,而是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因为孟子“道性善”,本身就不在于对性做客观的描述与分析,而在于将性看作人之为人之所在,通过对性的反省、自觉,确立人生信念,安顿精神生命,实现终极关怀。故孟子又从“天爵、人爵”、人格平等、“尽心、知性、知天”几个方面,进一步说明性善对人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1)“天爵、人爵”。人生在世,其价值、意义何在?除了财富、权势、地位这些世俗的价值外,还有没有一种更为根本、更能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存在?孟子通过“天爵、人爵”对此做了回答: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同上)
人爵指“公卿大夫”,即现实中的权势、地位;天爵指“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即内在的善性和对此善性的自觉、喜好。天爵的“天”有二义,一是指尊贵;二是指“此天之所与我也”。故天爵具有超越的来源,高于现实的人爵。古代的人将天爵置于人爵之上,“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体现了天爵、人爵的价值秩序;而今天的人修其天爵,是为了获取人爵,获取了人爵,便抛弃天爵,完全违背了天爵高于人爵的价值原则。所以在孟子看来,人的价值、意义不在于权势、地位,而在于善性、德性。人爵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得到,而天爵则是人人都具有的,是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赋予,这就保证了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价值与尊严,都有实现其价值与尊严的可能,从而确立起人生的信念与方向。“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同上)现实中,每个人都想获得尊贵,都希望得到社会和他人的尊重与认可,但往往忽略了自己本来就具有比生命还尊贵的善性,忘记了人的价值、意义首先是在于善性、德性;如果试图通过追求权势、地位获得尊贵,更有甚者,为了人爵放弃天爵,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犹)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公孙丑上》)
仁是天赋予我们的尊贵爵位,是人居住于其中的安宅。在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中,人爵服从于天爵,只要我们尊崇仁义,扩充、培养我们的善性,堂堂正正做个人来,自然便会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赢得他人的尊重。所以我们想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实现自我的价值,就应当反求诸己,从“修其天爵”、培养自己的善性做起,同时维护天爵、人爵的价值秩序。所以在孟子那里,性善不仅是人生的信念与方向,同时还是社会公正的基础。
(2)人格平等。在现实中,人与人是不平等的,这便是人爵得以产生的原因所在;但在不平等的现实面前,人们一直没有放弃对平等的向往与追求,所以古往今来许多思想家对平等做出深入思考与理论探讨。在儒家内部,首先对平等问题做出思考的是孟子,而孟子肯定人格平等,又是建立在“性善”论的信仰之上。
成覸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滕文公上》)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告子下》)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于人而疑之? 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上》)
“尧舜与人同耳。”(《离娄下》)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下》)
孟子将善性看作是人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而善性又是天平等地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只要扩充、培养我们的善性,“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便从根本上保障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可能。虽然“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滕文公上》),人与人之间存在能力、才智的差别,存在着财富、地位甚至是阶级的不平等,但在人格上又是绝对平等的。现实中的达官贵人往往以堂屋之高、饮食之美、饮酒纵欲、驰骋田猎之乐炫耀于世,以显示他们的特殊与尊贵,然而这些“皆我所不为也”,不是我所追求的;我所追求的是充分实现自己的善性,是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我的所作所为符合古代的理想之制,符合天爵高于人爵的价值秩序,所以即使面对在财富、地位上优于我的达官显贵,我也无所畏惧,依然可以获得一种平等感。孟子的人格平等,是一种内在平等,一种精神上的平等,不同于法律、制度上的外在平等,近代以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它可以转化为追求外在平等的精神动力,可以为法律、制度上的平等提供精神、信仰上的支持。
(3)人生之乐。性善论不仅保证了人格的平等,同时还使我们获得人生之乐,这是孟子向我们揭示的人性中最神奇、最奥妙之处。
孟子曰:“乐(音yuè)之实,乐(音lè)斯二者(注:指仁、义),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离娄上》)
孟子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
人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积极行善的时候,总能感到一种“乐”,这种“乐”油然而生,情不自禁,“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这最能说明善才是我们真正的性,虽然成为君子、善人还需经过后天的努力,但成为君子、善人是符合我们本性的,是我们扩充、实现善性的结果,用孟子的比喻,是“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相反,为恶则会戕害人性,使人感到不自然、快乐,成为小人、恶人只能是“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的结果。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如一个人做坏事,内心会扭曲,人格无法得到健康发展。现代心理学也证明,当人积极行善,处在友善的环境中,往往有利于生理、心理的健康发展,相反,若处在猜疑、敌视的环境中,则会出现心理失调,发育缓慢等不良后果。这些都说明,人生之乐、人生的价值意义只有在扩充、实现我们善性中才能实现、获得,而一味追求食色欲望并由此而为恶是不符合人性的,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人生之乐。对于统治者而言,教化和治理的主要任务不是强迫人们服从规范和教条,而是让人们“尽性”,尽情地发展、实现自己的善性;不是用严刑峻法威吓民众,而是“制民之产”,在提供基本生活物质保障的基础上,使每一个个体尽可能地充分实现自己的性,这一点在今天仍具有无比重大的现实意义。
(4)“尽心、知性、知天”。人生活在世界中,不仅面对人与人的关系,同时还面临人与超越者——在儒家这里是天——的关系,存在着“天道性命相贯通”的问题,后者涉及人生信仰、终极关怀等一系列问题,对人之存在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孟子“道性善”亦包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与思考,“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在孟子那里,天虽然是超越者,但它不是外在于人发号施令,而是内在于人之中,赋予我们心与性。所以扩充我们的心,实现我们的性,便可理解天,理解天的意志所在。同样,保存我们的心,养护我们的性,便是在侍奉天,是在尽我们的“天职”。这样,扩充、完成我们的善性便不仅仅是一种伦理活动,同时还是对超越者——天的回应,这种回应又反过来塑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赋予我们存在的终极意义,使我们在“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精神活动中,感受到自身的价值与尊严,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与使命,产生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的坚定信念。诚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孟子性善论,一方面为儒家成德之教提供了人性论的可能依据,另一方面也为儒家‘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形上信仰,建立了一套‘即内在而超越’的理解形态。”[7]所以孟子“道性善”虽然是一种人性论,但同时还关涉到与超越者——天的关系,是在天人关系的维度下展开的,可以说,孟子通过肯定性善保证了天与人的内在联系,使人与天的沟通、交流成为可能,从而为解决人生信仰,实现终极关怀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进路,其性善论又具有宗教性的功能与作用。
以上所论,便是孟子“道性善”的基本内容,包括了孟子对人性的内容与作用、人的价值与意义、人的终极关怀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人们之所以对孟子性善论感到不好理解,并产生种种误解,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没有从孟子自身的理路出发,没有用孟子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而是将后人的思维带入其中。例如,很多学者将“孟子道性善”理解为“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8]实际上《孟子》一书中只说“孟子道性善”“言性善”,而“道性善”“言性善”是宣传、言说关于性善的一种学说、理论,是不能直接等同于“人性是善的”。“人性是善的”是一个命题,是对人性的直言判断,而“性善”则是孟子对人性的独特理解,是基于孟子特殊生活经历的一种体验与智慧,是一种意味深长、富有启发意义的道理。理解孟子性善论,固然要重视孟子提出的种种理由与根据,更为重要的则是要对孟子“道性善”的深刻意蕴有一种“觉悟”,而这种深刻意蕴绝不是“人性是善的”这样一个命题所能表达的了得。如果一定要用命题表述的话,孟子“道性善”也应表述为:人皆有善性;人应当以此善性为性;人的价值、意义即在于其充分扩充、实现自己的性。
注释:
[1] 参见信广来:《〈孟子·告子上〉第六章疏解》,载李明辉主编:《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印行,第104~108页。
[2] 袁保新:《孟子三辨之学的历史省察与现代诠释》,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48~49页。
[3]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57页。
[4]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4~185页。
[5]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165页。
[6] 关于竹简“天人之分”与孟子“性命之分”的关系,参见第八章第一节:《竹简〈穷达以时〉与早期儒家天人观》。
[7]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0~67页
[8] 这种误解可能始于东汉王充,其《论衡·本性篇》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以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乱之也’。”
供稿: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