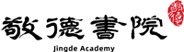“民本”与“仁政”
“民本”与“仁政”
一、 民本思想的论述
“民本”一词最早见于《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盘庚时期就有了“重我民”、“施实德于民”的认识。
《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尚书·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
《左传·襄公十四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左传·文公十三年》:“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亦,孤必与焉。”
《左传·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致力于神。”
《左传·僖公十九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 而况敢用人乎? 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
首次明确提出“以民为本”的是《晏子春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遗道;苟遗民矣,安有正行焉。”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的先哲们已经懂得民众对于国家政治统治的特殊作用。西周之初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劝诫国君要体谅小民“稼穑之艰难”(《尚书·无逸》)这通常被看作是先秦民本思想萌芽和产生的标志。
贾谊在《新书·大政》中提出:“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 吏以为本。”而且“民者,万世之本也”。
二、 民本思想与周代宗教的变革
王国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周人以“小邑周”的地位灭了“大邑商”之后,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在宗教观念上也进行了变革,一是提出天命靡常,认为“天不可信”;二是突出了民的地位,主张敬德、保民。原来在殷人的观念中,天乃神秘的外在力量,是历史与命运的主宰,它赐予并决定人世王朝的统治权力和政治寿命。当初殷人灭夏,就是遵行天的意志,“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汤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同上)殷人获得天命后,便会受到天的恩宠,并长久地保持之。“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盘庚》)所以当纣王身陷内外交困,不是及时自我反省,而是感慨,“呜呼!我生不有命于天?”(《西伯戡黎》)周人汲取了殷人的教训,不再一味地依赖天命,而是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注:文王)德延。”(《君奭》)天不可能长久地眷顾一族一姓,天曾降命、眷顾于夏人、殷人,但因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召诰》)。所以,“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只有像文王一样地敬德,才能保住天降于周人的大命。可见,获得天命的关键在于敬德,而敬德又主要体现为保民。在周人看来,“天惟时求民主。”(《多方》)“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泰誓》)也就是说,天赋予了君管理、统治民的权利,但这种“为民之主”的政治权利又主要体现为“保民”、“佑民”的责任义务。这是因为“惟天惠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天是民意的代表,是根据民意主张、行事的。既然天惠顾、同情民,那么,天所选立的君主自然也应该根据天的意志——实际也就是民的意志来进行统治,否则,便得不到天的认可,不具有统治的合法性。
与殷人的宗教观相比,周人是在前者天、君的二分结构中增加了民这一因素,突出了民意在宗教、政治中的作用,故陈来先生称之为“民意论”的天命观,认为是世界文化史上十分独特的现象。“在这样一种类似泛神论结构的民意论中,殷商以前不可捉摸的皇天上帝的意志,被由人间社会投射去的人民意志所型塑,上天的意志不再是喜怒无常的,而被认为有了明确的伦理内涵,成了民意的终极支持者和最高代表。”[1]对于周人天、君、民的三分结构,李存山先生曾设一比喻,认为其中实际潜含着三权分立的观念。“因为天的意志代表民的意志,而王又须按照天的意志来执政,那么民似乎具有立法权,王则行使行政权,而对王的选举、监督和罢免权则属于天。……在此结构中,人民并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利,其意志的实现要靠统治者对‘天’的敬畏、信仰或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的道德自觉。”[2]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与殷人相比,周人的天命观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主要是突出了民的地位和作用,将殷人的自然宗教发展为了伦理宗教。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周人的天命观也逐渐暴露出其不足,一是周人的天主要被少数统治者垄断,是其统治合法性的根据,而没有与个人发生联系,没有成为个人的终极信仰和精神动力;二是周人虽然突出了民意,但民还是一消极、被动的存在,不具有政治上的独立地位,其意志、意愿要靠神秘莫测的天来表达。特别是随着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周天子的权威名存实亡,天的观念逐渐受到怀疑甚至否定,统治者的私欲越发膨胀,民虽然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但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其生命、财产因诸侯间的连年征战而受到极大威胁。这时,周人的天命观已难以为继,在天、君、民的结构之外,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出现了,这就是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士”。作为新生的社会力量,他们一方面承继周人的天命观,将其中的“敬德”、“保民”转化为明确的政治理念——“仁”,将周人的政治伦理宗教转化为人生伦理宗教;另一方面,他们以“仁”的思想启发、教导君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希望通过“格君心之非”,做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同时为民的利益大声呐喊、呼吁,对暴君污吏的种种“残民”、“害民”等不义之举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抗议。可以说,孔子儒家是在神权衰落、王纲失序,君与民日益分离乃至对立的情况下,试图倡导仁政德治,将君、民重新联系在一起。对于君,他们是“师”也是“臣”;对于民,他们则是其代言人,是维护其利益的“民之父母”。
夏勇《中国民权哲学》:在我看来,“民惟邦本”是一个关于价值法则和政治法则的判断,也是一个关于人民的主体资格的判断,还是一个关于政治的合法性的判断。在价值法则方面,民本与人本是相通的,它们都把尊生爱人、保民养民作为最高的价值,把是否有利于人民作为最终的判断标准。在政治法则方面,民本与人民主权是相通的,它们都确认人民的主体地位,把人民答应不答应、同意不同意作为判断国家治理的政治标准。符合这样的价值法则和政治法则,统治者才具有合法性,正是基于这样的合法性观念,儒家得以通过义利之辨来抑制统治者的特权利益,在王霸之争上贵王贱霸,在君臣之际上提倡从道不从君。(7—8页)
到战国时,孟子将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高潮,提出了“民贵君轻”之说。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
孟子突出了民的地位,将其放在社稷(国家)、君主之上,认为“民为贵”。“贵”是贵重、尊贵之意,相当于今天所说“最为重要”,“最有价值”。故以上是说,人民与社稷和君主相比是最为重要,最有价值的,或者说,人民是国家的根基、基础,是国家的价值主体。这既是从国家治理的重要程度来讲的,也是对人民国家主体资格的肯定;既是一个事实判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是一个价值判断。孟子从长期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民心的向背往往决定着政权的兴衰得失,故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对于国家政权是最为重要的。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离娄上》)
不过,孟子的“民贵”说,不仅是对政权来源的认识、理解,同时也是对政权合法性的思考,认为人民的利益构成君主权力的基础,人民的生命、财产是最为珍贵的,是设立国家、君主的唯一理由与根据,君主应尽职保障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否则便不具有合法性。国家、君主的设立既然是为了民,是为了人民的需要,那么,“民贵君轻”便是自然合理的了。“民贵”说的前一个方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可称为“民心”说,主要针是对君主、统治者而讲的;后一个方面,则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一种价值理念和信仰,是孟子抨击暴政,“处士横议”的精神根源和动力,也是孟子民本思想中最核心、最有价值的部分。孟子“民贵”说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战国时期,诸侯混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之战,杀人盈城。”(同上)连年的战争,不仅给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沉重的灾难。到了战国后期,战争规模又不断升级,使广大民众饱受战争之苦。秦国攻打楚国的时候,秦将白起引水灌鄢城,淹死百姓数十万。统治阶级为满足穷奢极欲,想尽一切办法聚敛财物,广大民众却弃尸沟壑,挣扎在死亡在线。面对“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梁惠王上》)的不合理现状,孟子喊出了“民为贵”,指出人民的生命、财产是最为珍贵的,君主、社稷的设立都是为了民,并告诫统治者应保民、养民、富民,只有得民心,才能得天下。
由于“民为贵”,人民是国家的价值主体,人民的好恶决定政治的具体内容,“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君主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应注意考察民意,以官吏的任免而言,其进其退,都不能仅仅听取少数人的一面之词,而应以人民的意志、意愿为根据。他说: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下》)
甚至对别国的讨伐,也要征得别国民众的同意。在谈到齐国应否征伐燕国时,孟子提出:“取之而燕民悦,而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同上)将燕国民众的同意不同意作为出兵征伐的唯一的根据。更进一步,君主自身的统治,也应当得到“民”的认可。虽然孟子并不认为君主的权利是直接来自于民,而是保留了“君权天授”的形式,但其思想中显然也包含了对君主统治合法性的思考,认为惟有为“民”所接受和支持,君主的统治才具有合法的形式。换言之,民众的认可和接受,构成了判断、衡量君主统治合法性的尺度。孟子对“君”、“民”关系的这种理解,显然已超出了“君”应重视、关心“民”这一类简单的规定,而包含了对人民国家主体资格的肯定。孟子以舜继尧位为例,对此作了阐释。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
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注:音pù,显)之于民而民受之。 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子·万章上》)
孟子通过舜继尧位说明,天子之位既是来自天,又是来自民,是“天与之”、“人与之”,这是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孟子认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表明天下并非天子个人的私有物,“这种区分的内在含义,在于肯定天下非天子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之人或天下之民的天下。”[九]故在孟子看来,天子不过是受“天”与“民”委托的管理者,只具有管理、行政权,而不具有对天下的所有权。正因为如此,孟子肯定了汤武革命的合理性,不把君位看作是绝对的,如果君主不能保民,不能推行仁政,便可易位,甚至诛之、杀之。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同上)
同样,孟子也反对臣对于君的一味顺从,认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滕文公下》)。他向齐宣王进言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离娄下》)臣并不是完全依附于君,对于“贵戚之卿”来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这体现了社稷“贵”于君主);对于“异姓之卿”来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万章下》)。与君位相比,臣应更关注的是人民的利益与福祉,应该“守先王之道”、“乐道忘势”,应该直言进谏,为民请命,而孟子之所以有如此主张,显然就在于“民贵君轻”的价值理想与信念。
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将古代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高峰,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成就,不过其思想中仍具有一些时代的烙印,不可与后世的民主等而同之。这是因为,孟子虽主张“民为贵”,“君为轻”,但并不否认君主的特权地位,他认为君主的权力是“天与之”,是上天的赋予——尽管此天以人民的意志为根据,而一般的人想要成为天子,“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才可以实现。天子即位之后,除非残暴“若桀、纣者”,否则天也不会废弃。(见《万章上》)这是一种“君权天授”的思想,是一种神权政治,与近代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有所不同。同样,孟子虽肯定国家行政措施当以人民意愿为根据,认为人民的利益构成君主权力的基础,但并不主张人民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管理,并未赋予人民监督、节制和罢免君主的权利,孟子所关注的主要是人民的生存权(生命,财产)以及受教育权,而非人民的政治参与权。诚如梁启超所言:“孟子仅言‘保民’,言‘救民’,言‘民之父母’,而未尝言民自为治,近世所谓of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民有)、by the people(民治)之三原则,孟子仅发明of与for之二义,而未能发明by义。”与之相关,孟子肯定了社会等级的合理性,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 将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分工与政治学意义上的社会等级完全等而同之,由劳动分工的必要性论证社会等级的合理性,并赋予大人、小人这种社会等级以普遍的、永恒的意义(“天下之通义”) ,与现代民主制度下的平等观念显然也是不同的,因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之一,便是肯定每一合乎法定要求的社会成员都具有参与社会决策的权利,它的前提,则是承认每一社会成员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具有平等的地位。在这些方面,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与现代民主思想显然是有所不同的。
“仁政”与“王道”
孟子由“民为贵”进一步提出了“仁政”说,对孔子“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的思想做了进一步发展。孟子“仁政”说的思想基础是民本论,其根据则是性善论。孟子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
“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也就是人皆生而即有的仁爱、同情心。“先王”指尧舜和三代之王,孟子认为“先王”将生而即有的“不忍人之心”施之于社会政治中,于是就有了“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只要实行仁政,治理天下便可“运之掌上”。在孟子看来,推行仁政不仅富有成效,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原因就在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之君王与古之“先王”一样,也都有仁爱、同情之心。孟子在游说齐宣王时,以宣王不忍杀牛衅钟而“以羊易之”,“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启发齐宣王扩充此仁心,即可“保民而王”(《梁惠王上》)。孟子将仁政寄托在君主的不忍人之心上,似天真、不切实际,如后人所批评的,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但孟子以仁心启发宣王,不过是一种进言的策略,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无奈之举。孟子提倡仁政,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相信君王的不忍人之心,而在于坚信“民为贵”,认为人民的生命、财产是最为珍贵的,故以人民代言人的身份登上当时的政治舞台,要求统治者放下屠刀,实行仁政,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对于孟子而言,性善论只是实行仁政的可能条件,民本论才是其根本原因。故在《孟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孟子与齐宣王之间的另外一幕: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下》)
孟子从某人受人之托,照顾朋友的妻室儿女,却使其受冻挨饿;被任命为士师的高官,却不能管理好其下属,“则如之何”的一步步追问,意在提醒宣王注意,君主亦不过是受天之托来管理民众,如果“四境之内不治”,同样面临着“如之何”的问题。故在孟子看来,仁政决不仅仅是君主的一种施舍、怜悯,而是其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是其获得统治地位的理由和根据。而从“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表现来看,孟子的主张显然是宣王自己也无法完全否认的。
孟子通过总结三代“废兴存亡”的历史教训指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离娄上》)认为天子不施行仁政,便不能保全四海;诸侯不施行仁政,便不能保住社稷;大夫不施行仁政,便不能保住宗庙;士和庶人不施行仁政,便不能保全生命。他像孔子一样,一生中周游列国,游说魏、齐等国的君主,希望他们能效法尧、舜以及三代之王,“治民之产”,施行仁政,结束战乱,使人民过上安定、富裕的生活。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同上)
尧、舜等圣人是人伦的极致,是君道、臣道的最高榜样。后世当效法尧、舜,“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而尧、舜所体现的君道、臣道不过就是仁而已。孟子又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同上)认为施行仁政不仅要有善良之心和好的名声(“仁心仁闻”),同时还应有一套具体、可供操作的制度。只有其中的一项,“徒善”或“徒法”,都是不能真正实现仁政。只有“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也就是扩充不忍人之心,急民所急,想民所想,同时又“遵先王之法”,这样才能达到“仁覆天下”的效果。故在仁政的问题上,孟子不仅重人治,亦重法治,其所谓“法”主要是指“先王之法”或“先王之道”。孟子说: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梁惠王上》)
民众与士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具有了固定的“恒产”,才能有为善的“恒心”。如果没有“恒产”,人民生活陷入困顿,也就没有了“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所以先王、明君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设计相应的经济制度,使民众“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同上)。具体讲,就是要“正经界”,均井田;“薄税敛”,“省刑罚”;“去关市之征”,废除市场税等。孟子说:
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滕文公上》)
“正经界”就是要明确土地的所有权,避免暴君污吏对人民土地、财产的侵夺,故孟子视其为“仁政之始”,认为是施行仁政首先要做的事情。就孟子承认人民的土地所有权而言,他是肯定土地私有的。但春秋战国以来出现的土地私有,虽然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富国强兵,也暴露出相应的弊端,国家税敛无度,社会贫富分化,致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有鉴于此,孟子以恢复古代井田为名,提出了一个公有、私有相混合的土地所有模式,其具体内容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同上)在这个方案中,孟子既肯定了私田,也保留了公田。肯定私田,是为了鼓励生产,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保留公田,则是为了使百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讲,“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强调首先要治好公田,然后才能治理私田。但就施行仁政而言,他更重视的是私田,要求每家都有“百亩之田”可从事生产,统治者“勿夺其时”,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仁政、王道。孟子说: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
在人民有了“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后,国家还应“薄其税敛”,避免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孟子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尽心上》)他比较了夏、商、周三代的税法,认为“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滕文公上》)但相比较而言,“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是实物税,它根据若干年的收成确定一个平均值,不分灾年、丰年都按这一固定数字征收,实行起来比较刻板,不利于人民的生活。助是劳役税(“助者,藉也”),实行起来则比较灵活。故孟子主张“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同上)。孟子批评当时的统治者“不制民之产”,人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最终被逼无奈,以身试法。“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梁惠王上》)认为统治者等于是张着罗网捕民,哪有仁人在位却可以以网捕民的?所以真正的仁君、明主应“制民之产”,“薄税敛”,“省刑罚”,这样才能做到天下无敌。“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同上)
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已较为繁荣,出现了集市贸易,孟子主张“关市讥而不征”,反对统治者与人民争利,将其作为仁政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说: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公孙丑上》)
对于市场,提供空地储藏货物却不征税,如果滞销,就依法收购不让其长期积压。对于管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对于耕田的人,实行助法而不征税。对于人民的住宅,不征收额外的税钱。这样,天下之民便会欣然归附,“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同上)孟子对向市场征税之举十分愤慨,称其为“龙断”,并编造了故事,称率先向市场征税的人为“贱丈夫”。
孟子曰:“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公孙丑下》)
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梁惠王上》)。认为人的伦理生活高于物质生活,故在“制民之产”,人民的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后,便需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培养人民的向善之心。仁政、王道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富而教之”,实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上》)的和谐伦理社会。
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统一已成为大的趋势,对此孟子亦持肯定的态度。他曾转述与梁襄王的几句对话:“(襄王)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只有统一才能实现天下的安定。但当时各国都将统一的方式寄托在暴力上,希望通过“富国强兵”,“战胜弱敌”,当时形势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言,“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子则大义凌然地反潮流,“述唐虞、三代之德”,倡仁政,提出了“以德服人”的王道思想。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公孙丑上》)
孟子主张用“以德服人”的“王道”统一天下,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也就是反对法家以严刑峻法驱民耕战,凭借“富国强兵”的实力和暴力来统一天下。因为前者符合人民的普遍利益,体现了对人民生命、财产和意志的尊重,“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后者则是从统治者的个人私利出发,是为了满足统治者个人的私欲,相反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灾难,是违背人民的意愿的,它虽可以称霸一时,但不可长久。孟子说: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告子下》)
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上》)
“弃于孔子者”即违背了孔子、儒家的价值原则,具体讲,就是违背了“民为贵”的价值原则。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公孙丑上》),认为人民的生命高于君主、天下之位,天下虽大,亦不能以牺牲民之生命为代价。这当然是一种很高的人道主义和价值理想,夏禹、商汤,周文王实行仁政、王道,正体现了这种价值理想,而齐桓、晋文及当时之诸侯攻伐征战,违背了这一价值理想,“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孟子曾向齐宣王进言,称其试图用“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的方式,以实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无异于是“缘木求鱼”(《梁惠王上》),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只有实行仁政、王道,“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同上),才能真正统一天下。可见,仁政、王道不仅体现了“民为贵”的价值原则,同时还可以“得民心”,是富有成效,切实可行的。孟子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公孙丑下》)
孟子以商汤伐桀,“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梁惠王下》)说明“仁人无敌于天下”(《尽心下》)。他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公孙丑上》)基于这种认识,孟子甚至对《尚书·武成》篇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持怀疑态度:“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显然,孟子将正义战争理想化了,他的“以德服人”、“仁人无敌”的思想在当时也不免受“迂远”之讥。但孟子重视人民的力量,关心民众的疾苦,特别是将人民的生命、财产看作是最为珍贵的,认为任何统治者只有行仁政、王道,维护人民的生民、财产,才最有资格也最有可能统一天下,这种人道主义思想无疑是具有超越的时代价值,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历史的实际。
民本思想的意义:首先是从道德与政治的角度所确立的人民的主体性,从《尚书》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到《国语》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就生动地表现着这方面的思想内容。所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在人君上面的神,人君所凭籍的国,以及人君的本身,在中国思想正统的儒家看来,都是为民的存在……可以说神、国、君,都是政治中的虚位,而民才是实体”。“即就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不仅那些残民以逞的暴君污吏没有政治上的主体地位,而那些不能‘以一人养天下’,而要‘以天下养一人’的为统治而统治的统治者,中国正统的思想亦皆不承认其政治上的地位”(徐复观:《儒家对中国历史命运挣扎之一例——西汉政治与董仲舒》,《学术与政治之间》,第51~52页)。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不仅存在着君、相这样的现实主体,而且还存在着超越其上的以“天意”、“民心”乃至“神意”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主体性与人民的主体性。具体来说,虽然这种主体隐而不显,但实际上却是历史观念的真正主宰,也是历史评价的真正标准。因为只有这种主体,才是道德理想在政治领域的延伸,才是人民意志在历史评价中的表现。在现实地主宰着军政大权之君、相的背后,还存在着另一个主体——道德的主体与人民的主体。
其次,由于民本也就是人民主体性的存在,历史上的儒生如董仲舒等,往往能够与专制帝王做出种种抗争,他们坚持了“在人君的上面,另外还要拿出一个‘古’或‘天’压在他头上,使人君不能自有其意志,必以‘古’或‘天’的意志为意志;否则不配做人君,而可来一套‘革命’、‘受命’的”。对于历史来说,“由孔子在历史地位中之崇高化,使任何专制之主,也知道除了自己的现实权力以外,还有一个在教化上,另有一种至高无上,而使自己也不能不向之低头下拜的人物的存在。使一般的人们,除了皇帝的诏敕以外,还知道有一个对人类负责,决定人类价值的圣人,以作为人生的依恃,而不致被现实的政治,盖天盖地的完全蒙得抬不起头,吐不出气。所以,在中国历史中,除了现实政治之外,还敞开了一条人人可以自己做主的自立生存之路。”(同上,第333~334页)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之所以并没有完全走向由申、韩等法家所代表的极权政治,正是儒家以其道德的主体性与人民的主体性相抗衡的结果;而双重主体的矛盾,则不仅历史地说明了中国集权政治的具体形成,而且也生动的凸显了一代代志士仁人为了消解“双重主体”之间的矛盾所付出的努力。“我国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忠臣义士的流血流泪史。这些忠臣义士,一方面说明了他们以生命坚持了天下的是非;另一方面,则是汉以后‘君臣之义’的牺牲品”(同上,第387页)。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固然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集权政治确实很黑暗,——其真正的主体性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伸张,但也绝不是西化论者一言以蔽之的所谓“专制统治”就能完全说明的。
[1]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84页。
[2] 李存山:《儒家的民本与人权》,《孔子研究》2001年第6期。
供稿: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