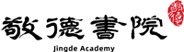敬德学刊
梁涛:“新四书”与当代经学的重建
周予同先生有一个说法: “ 经学的时代结束了,经学史的时代刚刚开始。 ”虽然说是经学史研究,但周先生及弟子朱维铮先生对于经学基本是否定的态度,这很难说是客观、公允的研究。如果我们今天还是采用这样一种态度,还是周予同、朱维铮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自绝于时代、自绝于学术界,必将走进一条死胡同。姜广辉教授主持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课题研究前后历时十三年,《中国经学思想史》四卷六册终于于2010年出版,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这项研究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经学正名,为经学翻案。姜广辉先生提出了“根”和“魂”说,认为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经学的价值是中国文化的魂。所以对待经学,我们不能是整理国故的态度,视其为博物馆中没有生命的陈列物,而应看做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价值体系、精神家园,经学研究也不应只是把经学当作一种古董知识来了解,不只是对经学演变的轨迹作历史性的陈述,而应把它当作中国古代价值理想的思想血脉来理解,通过经学注疏透视其时代的精神和灵魂。经学不仅是一套知识体系,同时还是一种价值信仰,今天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重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使经学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重新发生关联。
中国传统的经学主要分汉学和宋学,汉学重视五经,宋学突出四书。在笔者看来,五经是前转轴时期的文化积累,四书则是转轴时期的文明创造雅斯贝尔斯有转轴时期的说法,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这一时期,世界几大古代文明都出现突破性发展,奠定了人类自我理解的框架和基础,以后每一次飞跃都要回到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点燃。但中国文化的特殊之处在于,她不仅有一个灿烂的转轴时期,还有一个漫长的前转轴时期,因此转轴时期是春秋战国,前转轴时期则是尧舜和夏商周三代。以后每一次飞跃不仅回到转轴时期,同时也可能回到前转轴时期。汉唐是回到前转轴时期,重视的是五经,故周孔并称,孔子附属于周公之后。宋明以后,则是回到转轴时代,四书地位提升,故孔孟并称。当前的经学研究五经面临的主要是历史观问题;四书则是哲学或义理的问题。章学诚说“五经皆史”,但在传统社会中五经不同于史,二十四史不能与五经相提并论。从经学史看,经之为经,一是因为唐虞、三代是理想社会,五经记载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王的事迹,是三代理想社会的典章法规、制度成法,这与后世的“相斫书”是不同的——这一般是古文经学的看法。二是五经经过孔子的删订已把儒家的一些基本价值观体现在里面了,故经之为经不在于文献本身,而在于孔子赋予其特殊的“义”,“其义丘窃取之也”——这一般是现经学家的看法。但这两点在近代基本被否定掉了。
首先是古史辨派的兴起,顾颉刚提出层累地构成古史说,认为五经所记载的内容都是后人的伪造,是后人添加上去的,比如禹是一条虫,尧舜等可能也不存在等。古史辨通过否定三代历史进一步否定了儒家经学的价值理想。如果儒家的理想是建立在一个根本不存在或者虚幻不实的历史上,从当时科学主义的眼光看来自然就失去了合理性。其次是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传入,按照这种理论,三代就是奴隶社会,是落后反动的。儒家推崇三代、周公就是在开历史倒车,是复辟、倒退,这样儒家经学的权威也就被消解了。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经学,首先遇到的就是经学与史学的关系问题,是历史观的问题。只有搞清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对经学重新定位,重新看待经学的价值与意义。
古人是有自己的哲学和思想的,而他们建构自己的思想则是通过经学诠释的方法,通过与经典的不断对话,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然后又用其思想去诠释一部经典,朱熹、王夫之、戴震等无不是如此,这就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所以中国的诠释学跟西方不一样,我们往往是有了自己的思想之后,用自己的思想去解释经典,把自己的思想贯穿在经典之中,通过对经典的诠释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是中国诠释学的特点。朱熹的《四书集注》到底是孔子、孟子的思想还是朱子的思想?王阳明的《大学问》到底讨论的是《大学》的思想还是阳明的思想?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到底是孟子的思想还是戴震的思想?这是很难分得清的,往往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所以余敦康先生说,如果我们今天想发展儒学、建构思想体系,恐怕还要回到传统经学中去。
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个看法。香港中文大学的刘笑敢教授就提出,中国哲学至少有三个身份:现代学科,民族文化,生命导师;两个定向:面向历史的、文本的定向和面向现实、当下的定向。我们在哲学史研究中,一方面是要回到文本、回到历史中去,客观地把握文本的原义;另一方面则要有一种现实、当下的考虑,甚至是未来的展望。这两种定向间有一种张力。作为现代学科,中国哲学研究面对的是文本、历史;而作为民族文化,其关注则是现实、当下;至于生命导师,主要是对普通民众的宣教,如于丹等人所做的工作。刘笑敢教授认为中国哲学界的混乱就是没有把这三种角色分开来,他尤其反对将自己的思想强加到经典中去。你明明是要建立二十一世纪的哲学,为什么一定要说是古人已有的?明明是要创造当代的哲学体系,为什么一定要套上古人的思想?这样套的结果,一是对文本的原意做出附会和扭曲,二是束缚你自己的思想。自己讲、讲自己不是更好吗?抛开了经典的束缚,不是更有利于思想的创造吗?刘教授承认中国古代有一个通过经典诠释创造思想体系的传统但是他怀疑这个传统在今天是否还适用?是否还以继续作为我们思想创造的形式?对于刘笑敢教授的说法,笔者是不接受的。按他这个说法,我们今天建立新经学就不可能了。
笔者的看法是,今天每一位学者当然可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比如安乐哲的哲学、杜维明的哲学、成中英的哲学等。但是这些内容按中国传统学术的划分来看,只能算是子学,而子学是不可能代替经学的。经学是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是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它是子学的源头,其地位是更为重要的。每一位哲学家的思想创造都是通过与其民族最基本的经典反复对话来完成的。从这点上来讲,经学还是必要的,经学和子学是不矛盾的,子学不能代替经学,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中,经学依然要发挥其《论语》,汉代人读,唐人也读;宋明人读,今人也在读,一百年后也还有人读,但理解是不一样的,不断有新的问题出来,有新的诠释。根据西方施特劳斯学派的观点,经典诠释不是探讨苏格拉底、柏拉图讲了些什么,而是像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去思考,去寻找历史上一个个的柏拉图时刻、苏格拉底时刻。对中国来说,就是寻找中国历史上的孔子时刻、孟子时刻、荀子时刻。如果孔子、孟子、荀子生在今生今世当做何思、当做何想?就这点来看,经典的意义当然是无限开放的,不可能被束缚住、被穷尽了,随着人们问题意识的变化肯定有不同的读法,有新的诠释,不好说哪一个是更为客观的。
所以,正如当年宋儒通过经典诠释重建儒学体系、压倒佛老、复兴儒学一样,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借鉴宋儒的方法,完成当代儒学的复兴和重建宋儒的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道统说的提出。唐代韩愈提出道统说,认为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一直有一个道统,这个道统经孔子传给子,曾子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轲,孟轲之后就不传了。这一看法被理学家如朱熹等人继承下来,成为主流的观点。其实,孟子之后还有荀子,还有汉唐儒学,为什么说孟子之后道就不传了,中断了?这与对道的理解有关。朱子的道统说是一个哲学、超越的说法,道是永恒、超越的价值理念,其核心是仁义,而仁义又体现为心性或性与天道的问题。
要体现在具体的经典中,那么,哪些儒家经典能够反映儒家之道的精神呢? 这就是四书。其中,《论语》记录孔子思想,《大学》是曾子,《中庸》是子思,《孟子》是孟子。所以,四书与道统说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三,儒家哲学的探讨。宋儒注经不同于汉儒的章句之学,不仅是一种注疏,而且是一种哲学 诠释。他们借鉴佛老的形上思维,通过对理气、心性、已发未发、格物致知等概念的细致辨析,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按照学界的最新看法,宋明理学可分为四派:理学、心学、气学、性学。这些派别的不同实际是哲学建构的不同,体现了对宇宙本体、价值根源的不同认识和理解。第四,经典诠释 的具体实践。根据各自的哲学思想和义理架构,对儒家经典进行诠释,如朱子注释《四书》等等。宋儒的方法是值得借鉴、学习的,但其具体内容和看法则需要作出重新检讨。首先是道统说。朱子认为,只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代表了道统,他们的思想一以贯之,传递着相同的道,是否符合事实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由于郭店竹简等地下文献的发现,我们认识到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子、荀子,实际是儒家内部的分化过程,子思的思想固然影响到孟子,但与荀子也存在一定联系,术史上虽然并不存 在 一 个 思 荀 学派,但从思想的联系来看,子思的思想同样对荀子产生过影响和启发。分化的好处是深化,如孟子对孔子仁学做出进一步发展,提出性善论、浩然之气等等,荀子则对儒家礼学做出更多继承和发展,并援法入礼,开启了儒法合流的趋势等;其不好的地方则是窄化,不论是孟子还是荀子都没有代表整个儒学传统,而存在“所失”或“所偏”。因此,将道统仅仅限定在曾子、子思、孟子等少数人显然是不合适的,如钱穆先生所批评的,“是一种主观的道统”,“一种一线单传的道统”,是“甚为孤立的,又是甚为脆弱,极易中断的”。
另外,朱熹继承韩愈的看法,将道统的内容理解为仁义,并将其还原成心性、性与天道的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在早期儒家那里,仁学与礼学是一个整体,完整的仁—礼之学才是儒家的真道统。从这个角度去看孟子有所失,他重视内在仁义,对外在礼仪有所忽略;荀子则有所偏,他偏于礼乐制度,内在仁学则有所欠缺。故将道统限定在曾子、子思等少数人,或以孟子为正统排斥荀子都是不合适的。只有统和孟荀,恢复早期儒学的丰富传统,才能建构起儒家的真道统。
那么,如何表达儒家的道统呢?笔者觉得传统的“内圣外王”一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儒家之道即内圣外王之道。其中,内圣相当于仁学,指内在主体和精神超越;外王相当于礼学,指外在制度和礼仪法度。在周公和孔子那里,内圣外王实际包括了由内圣而外王和由外王而内圣两个方面,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以后孟子主张“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实际是由内圣而外王;荀子提出“明分使群”、“化性起伪”,则是由外王而内圣。由于宋明理学家推崇孟子,其所理解的内圣外王主要是由内圣而外王,突出的是内圣之学,而忽略了荀子所代表的由外王而内圣。其实后者也是儒家道统的一个重要内容,代表了儒家的外王学。所以统合孟荀,尤其是补上由外王而内圣的路向,才是完整的儒家道统。
其次是经典的选择。如果说《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是旧道统的产物,并不能完整反映早期儒学的丰富传统,那么,与新道统相应,则应对儒家经典做出重新选择。在笔者看来,能够反映早期儒家文化精神与生命的应该是《论语》、《礼记》、《孟子》、《荀子》四部书,可称为新四书。其中《礼记》代表了七十二子及其后学的思想,《大学》、《中庸》本来就是来自《礼记》,现在将其放回《礼记》。而《礼记》中的其他各篇,如《礼运》等都是理解早期儒学的重要篇章。对于新四书,我们也不是将其内容看作是一以贯之、彼此一致而没有分歧的,应该认为其反映了儒家文化生生不息、成长、发展、曲折、回转的过程。无论孟子还是荀子都无力独自承担儒家的道统,只有统合孟荀、互为补充,才能够重建道统,恢复儒学的精神生命和活力。孟荀思想中的某些对立或分歧,恰好使其相互补充成为必要。故读《孟子》须兼《荀子》,读《荀子》须归于《孟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对儒家哲学的探讨以及经典的诠释实践,在于确立儒家的精神本体,并以此精神本体对儒家经典做出创造性诠释。正如当年宋儒出入佛老数十载然后返之六经,借鉴佛老形上思维,通过对四书的创造性诠释完成儒学的伟大复兴。我们今天也应借鉴宋儒的方法,重新出入西学数十载,然后返之于六经,以新道统说为统领,以新四书为基本经典,“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以完成当代儒学的开新与重建。什么是“六经注我”?就是以“六经”的价值、意义注入到“我”的生命中,滋润了“我”,养育了“我”;什么是“我注六经”?就是将“我”的时代感受、“我”的生命关怀、“我”的问题意识带入到“六经”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六经皆史”——“六经”是一部民族成长、发展的历史,是精神的历史、自由的历史。此精神、自由之历史才是儒家道统之所在,是孔、曾、游、思、孟、荀精神之所在,也是新四书所要解决的问题。
供稿: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