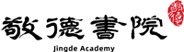敬德学刊
儒学心性论的历史进程

[摘要]儒学心性论在历史上有一个相循相续的发展过程,孟子强调心性的合一性,荀子突出心性的相分性。程朱认为心性通而不同,有荀学的痕迹;陆王坚持心即性,以孟学为旨归。在现代新儒学中,冯友兰走的是程朱的路,其学是程朱之学的延伸,熊十力、牟宗三走的是陆王的路,其学是陆王之学的发展。
心性论也可称为心性之学,是关于心性的理论或学说。中国哲学虽然是围绕天人之际展开的,但是天人之际的核心不是天,而是人。而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心性问题。所以心性问题一直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一项基本理论。对于心性的不同理解和说明,是儒学内部派别分歧的重要表现,甚至可以说是儒学内部派别划分的主要标志。从心性论的历史演变,可以清楚地检阅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
作为儒学的开山始祖,孔子还没有确立完整的心性论。孔子没有论及心,论性也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 ·阳货》)孔子一生讲得最多的是仁。然而孔子论仁,主要局限于仁本身,即仁是什么,为什么行仁的层面上。至于如何行仁,在孔子那里,还不是问题的重点。孔子只是简单地说:“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行仁完全是人的自觉的行为。至于为什么是人的自觉的行为,孔子并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证。虽然孔子也讲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人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然而推己及人一般只具有操作上的意义,并不具有理论根据方面的因素。
孟子处处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孟学对于孔学的发展,主要就在于“为仁之方”方面的发展。如果说,孔学的重心还停留于仁本身,还停留于仁是什么、为什么行仁的问题上,那么,孟学的重心则由仁本身转向“为仁之方” 。孟子自觉地将孔子仁学的终点作为自己仁学的起点。并通过对“为仁之方”的论述,而建立了自己的心性论。以心性论为基础的“为仁之方”的理论,既是孟学对于孔学的最大发展,也是孟学之为孟学的主要内容。
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人与动物之间是有相同性的:“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嗅也,四体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尽心下》)人与动物相同的因素是性,但却不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不是人性。孟子认为,人异于动物的根本所在,在于人先天地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才是所谓的人性。“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在孟子看来,人性与人心本是二而一的东西,人性即是人心,人心即是人性。从人之所以为人的角度,从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天赋的角度看,是人性;从其居于人的内心,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角度看,则是人心。因此,人的本心、本性就其本原意义而言,原本就是善的。[1]这种本原的、先天性的善,正是人为仁向善的基础;人本身原有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正是人为仁向善的发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并不是外在于人或强加于人的东西,而是根源于人心、人性,并且是由其发育出来的东西,是人心、人性中本有的东西:“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这种心性论的确立,就为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第一次寻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

性善论是仁义之道得以实行的先天根据。但只有这个根据还不够。在孟子看来,一个人要真正成为仁人君子,还必须使自身本有的善端得以发扬广大。“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孟子·公孙丑上》)扩充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尽心”,一是“养气” 。孟子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尽心”就是尽力发扬自身本有的善心。“尽心”即可“知性”,“知性”即知其性之善。而性根源于天赋、来源于天赋,所以“知性”则可以“知天”,“知天”即知天之善。而由天之善进而可知天之理。这样,性一方面具有主观自我的因素,它是我之为我的根本所在;另一方面又具有外在客观的因素,它根源于天赋自然。从而,性便成了连接心(主观自我)与天(外在客观)之间的桥梁。孟子通过性,将宇宙人生打成一片,实现了物与我、天与人之间的融通和贯注。如果说,“尽心”是由内而发外,由己而及物;那么,“养气”则是聚外而凝于内,由物而及己。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所谓“浩然之气” ,即是天地间的一种“至大至刚”的正气。这种正气流荡于天地之间,是天地之善的具体表现。“养气”,就是要使这种正气凝聚于身、于心,并使其发扬光大。通过“尽心” 、“养气” ,孟子既找到了一条现实的修身之道,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实现了天与人的沟通与贯注。
孟子的心性论以性善为基础,以心性不二为核心,以天人贯通为特征。这种心性论,其先验论的色彩是非常凝重的,这是其无法克服的弊端。但是这种心性论的确立,在儒学发展史上,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在于它弥补了孔子仁学的缺憾,为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第一次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从而使其真正变得切实可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将人与天、自我与外物沟通联结起来,从而将宇宙人生打成一片。孟学对后世儒学的影响、孟学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主要即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
如果说,心性不二是孟学的核心,那么,心性二分,以及由心性二分而引起天人二分,则是荀学的基本特征。孟子把心理解为人之为人的本心,与此不同,荀子则把心理解为感官之心。荀子说:“治之要在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荀子·解蔽》)有时候,荀子也把心理解为身之主宰。如其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同上)然而,不管是感官之心,还是身之主宰,在荀子这里,心只具有主观性,心与性是没有关涉的。

虽然荀子也像孟子一样,认为性是人秉受于天的,是先天的,是天赋的。但是与孟子不同,荀子将人与动物所共有的好利恶害的自然本性,当作基本的人性,从而得出了人性恶的结论。从而人身修养的过程,在荀子看来,完全是一个“化性起伪”的过程。“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性情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荀子·儒效》)虽然不能说,“化性起伪” 、“慎俗” 、“积靡” ,在人格修养上就没有意义,但是由于这样一种心性论辟心性为二,没有将性限定在人之所以高于动物族类的属性上,并由此而导致了天人的截然二分。所以,荀子的心性论,在儒学的发展史上,长期是被当作异端来看待的。
二
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史上的新阶段,其基本课题就是对先秦儒学所提出的人伦道义作学理上的证明,从而从理性方面论证儒学所提出的纲常名理的恒常性和神圣性。宋明理学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即是将天、地、人之间的关节打通,将它们贯通起来,并认为这其间存在着以一贯之的东西。这种以一贯之的东西,在宋明理学看来,就是所谓的“理”。这是宋明理学诸主要代表的共有倾向,也是宋明理学理论上的基本特征。然而,在天人贯通的具体途径上,特别是在对于人的心性的理解方面,宋明理学内部却有着很大的分歧。一派看重心性间的差分,从而认为天人之间的相通是一种间接的相通;一派则强调心性的合一,从而认定天人之间的相通是一种直接的相通。前者最主要代表是程朱,后者最主要的代表则是陆王。
应该承认,程朱在学理亘续方面,是自觉地接续孟而贬斥荀的,特别是朱熹。孟子在儒学史上的“亚圣”地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与朱熹的《四书集注》有很大关系的。然而,在心性论方面,与其说程朱近孟而远荀,毋宁说程朱近荀而远孟。
首先,在对于性的理解方面,程朱与孟有偏差。孟子对于性的基本理解是性即天,即人之天。程朱对性的基本理解是性即理,即天之理。程颐说:“性即理也,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程氏遗书》卷十八)朱熹说:“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孟子集注》卷十一)在孟子看来,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本身即是人之性。而朱熹则明确指出:“仁义礼智,性也,体也;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情也,用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虽然程朱也承认人与天的必然联系,但是,人与天的必然联接,在孟子那里(通过性即天)是一种直接联接,而在程朱这里(通过性即理)则是一种间接联接。
其次,在对于心的理解方面,程朱远孟而近荀。孟子对心的基本理解是心性不二,性即心,心即性。程朱对心的基本理解则与荀子相近,认定心不过是感官之心,不过是身之主宰。程颐说:“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程氏遗书》卷十八)朱熹更为明确地指出:“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五)诚然,程朱也认为心性之间是有关联的。程颐说:“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程氏遗书》卷二十五)具此,很多人认为程颐也主张心即性。其实,这里的“一”并不是同一的“一”,而是一贯的“一”,也就是说,心性之间虽有关联但毕竟还是二而不是一。对此,朱熹有更清楚的说明:“心性固只一理,然自有合而言处,又有析而言处。须知其所以析,又知其所以合,乃可。然谓性便是心,则不可;谓心便是性,亦不可。”(《朱子语类》卷十八)在孟子看来,心即是人之先天的本心,即是人之义理之心;性即是人之所以为人者,即是人的先天的本性。所以,心即性,性即心。而在程朱看来,性是“人之所得于天之理”,心是“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所以,心、性虽有联系,但毕竟心是心,性是性。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程朱辟心性为二,并认定天人之间的必然联接非直接而间接,所以,程朱认为人身修养的过程就是一个“格物致知”的过程。而这种“格物致知”,通过格物──穷理──致知──反省自身,从而达到心灵的冥识契悟,从根本上来讲,与孟子所倡导的“尽心”,在本心上作功夫是不相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格物致知”似乎更接近于荀子的“积靡”和“化性起伪”。虽然程朱的根本用心还在于“明理”,但是格物的危险却在于由此而使心逐于物而不明理,或虽明理而不得其全而流于支离,从而从根本上背离初衷而使自己处于飘浮状态。对于这一点,在鹅湖之会上,陆氏兄弟已经指出了朱学的这种流弊,清代颜元更指出:“千余年来,率天下入古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朱子语类评》)颜元之语也许有激愤之意,有过其实之嫌,但却并非无中生有,而可以说是切中其弊。

与程朱不同,陆九渊和王阳明以心性不二、心理不二、发明本心为自己理论的基本主旨。如果说,在程朱那里,还只承认“性即理”,但却否认“心即性”,从而“心”与“理”还流于二,[2]从而在“理”上作功夫,那么,陆王不仅认定“性即理”,而且坚持“心即性”,从而导出“心即理”,这样就将孟子的心学与程朱的理学遥契勾连起来。陆九渊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与李宰书》)王阳明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传习录》中)
由于“心即理”,由于理本来就居于心中,因此,与程朱在“理”上作功夫不同,陆王把功夫只放在“心”上。这种功夫,在陆九渊那里,就是所谓的“切己自反”。“义理之在人心,实天之所与,而不可泯灭者也。彼其受蔽于物而至悖理违义,盖亦弗思焉耳。诚能反而思之,则是非取舍盖有隐然而动,判然而明,决然而无疑者矣。”(《陆九渊集·拾遗》)修身的功夫就是反思去蔽、恢复本心的过程。这种功夫,王阳明把它叫作“致良知”。“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物格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传习录》中)对程朱而言,本体是善性、是天,而功夫是格致,因此,本体与功夫、天与人是有区别的;而对陆王而言,本体在心,功夫也在心,所以,本体与功夫、天与人是没有严格区别的,是融为一体的。
程朱修身论的路径是由外而内,陆王修身论的路径是由内而外。前者似乎更接近荀学,而后者则更接近孟学。两者各有利弊,对此很多人看得很分明。如元代的郑玉说:“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明;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陆氏之学,其流弊也如释子之谈空说妙,至于卤莽灭裂,而不能尽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学,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寻行数墨,至于颓堕萎靡,而无以收其力行之功。”(《师山文集》)理想的途经应当是将两者融会贯通起来。而从天人契合的角度看,陆王之学则似乎更看重、也更易于实现天人之间的相契与贯通。
三
现代新儒学是以宋明理学的后继者自期自命的。宋明理学探讨的主要问题,在现代新儒学这里都有新的发展。在心性论方面,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冯友兰借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以新实在论哲学为蓝本来改造、重建程朱理学。在冯友兰看来,“理”是一事物之所以成为某事物的原因或根据,“自其因依照某理而得成为某一类事物言,则谓之性。”(《贞元六书》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所以,性即理。而“所谓人性者,即人之所以为人,而以别于禽兽者。”(同上书,下,第541页)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觉解。觉是自觉,解是了解。“人之所以能有觉解,因为人是有心底。”(同上,第533页)所以,在冯友兰这里,理、性、心也是相互关联、一一贯通的。但与程朱一样,心与性,在冯友兰看来是通而不是同。同是同一个东西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称谓;而通则是不同东西的彼此贯通。另外,与孟子将性理解为人的先天的道德理性不同,冯友兰将性只理解为知性。从而,天与人的关系,从初始状态来看,还是分而有别的。天与人之间的贯通与融合,在冯友兰这里,是通过知性上的自我觉解而达到的心灵境界来实现的。
冯友兰认为,人对于宇宙人生觉解的程度,可有不同,由此,宇宙人生对于人的意义,也有不同。这种不同的意义,即构成不同的人生境界。人生境界由低向高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作为最高的人生境界,其特点是:“他已完全知性,因其已知天。他已知天,所以他知人不但是社会的全的一部分,而并且是宇宙的全的一部分。……他觉解人虽只有七尺之躯,但可以‘与天地参’;虽上寿不过百年,而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同上,第557页)这样,天与人,虽有分别,但完全可以通过人的自我觉解而实现其贯通与融合。

与冯友兰不同,熊十力通过对西洋哲学本体论的儒化改造,将宇宙论、人生论、道德论打成一片。西洋哲学家讲本体,大抵把本体当作离人而外在的物事的共相、形式。熊十力以为,本体并不是脱离吾心而孤立的境界,他在谈到《新唯识论》的宗旨时指出:“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学着令知一切物的本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7页)本体不外于吾心,本原亦不外于吾性。“万物本原与吾人真性,本非有二。”(同上书,第251页)在熊十力看来,本体自身虽是无形相的,但却遍现为一切物事,化为一切势用。所以,“体用不二”,用即体,体即用。生生不息,大化流行,是宇宙万物的生命本原,也是吾人之真性,是吾人之所以为人之真宰,当然也是吾人与天地万物同具之本体。这种本体,既不是纯粹的自然本体,也不是纯粹的精神本体,而是一种生命本体,是人与天地万物共同依存的根据。所以,在熊十力这里,我之本心、本性与物之本体、本原,不仅是息息相通的,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据此,熊十力对程朱理学割裂心性的作法,提出了批评:“宋明理学家有以为心未即是性者,此未了本心义。本心即是性,但随义异明耳。以其主乎身曰心,以其为吾人所以生之理曰性,以其为万有之大原曰天……故尽心,即是性天全显。”(同上书,第252页)虽然熊氏在这里并未明确道出否认心即性者就是程朱,但其意还是比较明显的。后来牟宗三则直接表达了此意。在熊十力看来,人与天、人道与天道、人之生命与宇宙大生命,既不是无所关涉的两极,也不是静态的、凝固僵化的两极。而是同体同原、相通相契、无有阻隔的。由天而人,这是天道流行;由人而天,这是赞天地之化育,也就是道德修为、道德践履。由人道可以征得天道,由天道可以弘扬人道。生生不息是宇宙的大生命,是人的真性、真宰,因此,自强不息也就是人的真生活、真道德。如果说,在宋明理学那里,人与天之间还须依靠理、性为中介,联接、勾通起来,那么,在熊十力这里,人与天本身即是合为一体的。天道即人道,宇宙即人生,体道即修行。由此,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道德论,完全是合而不分的。如果说,孟子的心性论是一种先验唯心论,那么,熊十力唯识论的心性论则是一种彻底的主观唯心论。
牟宗三是熊十力自觉的、直接的继承者。同熊十力一样,牟宗三哲学的重心也是重建本体论,重建哲学行而上学。在牟宗三看来,哲学形而上学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寻求对于自然宇宙的某种纯客观的解释,而在于揭示宇宙人生的终极意义和终极价值,并由此确立人的终极关怀和终极信念。同熊十力一样,在学术理脉的传承亘续方面,牟宗三是自觉地背弃程朱而亘续陆王的。牟氏认为,否认心即理,主张心、性、情三分的程朱理学,割裂了内在与超越、存有与活动的关系,从而无法确立道德行为的内在根据,无法说明道德主体的“自主、自律、自决、自定方向”,充其量只能成就一种他律的道德。
牟宗三承续陆王,重建哲学形而上学的具体作法,就是将儒学心学派的基本义理嫁接在康德道德哲学的枝杆上,从而使其焕发出新的时代气息。牟宗三非常欣赏康德关于道德法则的先天性和普遍性的论证,认为这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基本灵魂。但是,作为道德行为生发的内在根据的道德理性,即自律自由的意志(善良意志),在康德看来,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公设”,只是“理上应当如此”,至于事实上是否如此,乃是人的理性所无法证明的。所以先天普遍的道德律只具有“应当”、“命令”的性质,并不具有“实然”的属性。牟宗三认为,这是康德哲学的大误所在。在牟氏看来,道德理性之存在不是一种“理论的公设”,而是一种“定然地真实”,是真实的“呈现”。因为它就是“人人所皆固有的性”,是人的内在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者。牟宗三指出:正宗儒家讲性的密意,正是肯定道德理性、意志自律是定然的、真实的、呈现的。惟其如此,道德法则、道德行为才有了可靠的根基和根据。“儒者所说之‘性’,即是能起道德创造之‘性能’;如视为体,即是一能起道德创造之‘创造实体’。”(《心体与性体》[一]台北正中书局1973年版,第40页)一方面,这种性与天道是通而为一的。它来自天道,同时也参与天道,它是即内在即超越的。从内在的层面讲,它是道德实践何以可能的根据;从超越的层面讲,它又是天道、天命的具体流行,是天道、天命在人身上的实现。另一方面,这种性又与心是和而为一的。心与性本是一体而二名,“客观地言之曰性,主观地言之曰心。自‘在其自己’而言,曰性;自其通过‘对其自己’之自觉而有真实而具体的彰显呈现而言则曰心。”(同上书,第42页)
牟宗三通过将儒学义理嫁接在康德哲学枝杆上,既提供了道德实践何以可能的内在根据,又在新的基础上,以性为中介将天与人、天道与伦理重新联接起来。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嫁接,使两者的优长得到了互补和发挥。既克服了康德哲学义理上的不足,也克服了传统儒学缺少严密的逻辑论证,以及缺乏概念的明晰性的弊病。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心性、天人问题上,从孟子到荀子,是由合到分;从程朱到陆王,是由分而和到和而合;冯友兰坚持分而合,是程朱之学的延伸;熊十力、牟宗三坚持和而合,是陆王之学的发展。各派之间有异亦有同,甚至其所同更大于其所异。正是通过这种同异的历史变迁,使得这一问题不断得到深化与发展。可以说,儒家心性论所传达的基本精神就是天与人、宇宙与人生、天道与伦理之间的相互贯通。儒家从来不孤立言天。言天即是言人,言宇宙即是言人生,言天道即是言伦理。儒家总是将宇宙人生打成一片。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性。性既是勾通、联接天、人两端的中介和桥梁,也是道德实践得以生发的内在根据。坚持天人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贯通,是儒学以至中国哲学的基本宇宙观。这一宇宙观比起西方的天人二分的宇宙观,自有其优长之处。而这一宇宙观的核心内容,正是心性论。面向21世纪,在科学至上主义横行、工具主义泛滥、狭隘人类中心主义已经带来灾难性后果的今天,儒家哲学之天人论、心性论,是有其时代价值的。仔细考察儒家心性论的历史演变,探究其可能的现代出路,重新确立人类价值系统,发挥哲学所本有的“安身立命”的特殊功能,当是现今研求哲学者所不能推卸的责任。
【注释】
[1] 对于孟子的性善论,向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性本善,一种是本性向善。两说虽都有一定的根据,但“本善”是根据,“向善”是功能,无有根据,功能亦无从发挥。所以孟子言性善,主要是从“本善”立论的。
[2] 虽然朱熹亦有“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朱子语类》卷九)之语,但在朱熹那里,心虽然可以“包”理,但毕竟心是心,理是理,理与心从本原而言,是分不是合。朱陆差分的关键不在于能不能合,而在于合是结果还是本然。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 罗安宪
(编辑:杨阳)
供稿: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