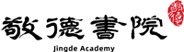书院,北京历史文化的一道风景
1
谈起北京历史文化,人们通常说得比较多的,无非故宫、天桥、胡同、会馆之类。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北京历史文化中固有的、色彩鲜明的元素。但只有这些似乎还不能使北京历史文化得到充分的体现。细想起来,有一个群体,人们很少提到,即生活于北京地区的学人士子和士大夫。究其原因,我以为,也许是没找到一个可以体现这个群体存在价值的社会载体。就像人们说皇家文化有故宫,说市民文化有天桥,说京味文化有胡同,说名家文化有会馆一样,说学人士子和士大夫文化,也需有个依托和承载物。于是,书院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北京自辽金起就是都城,其中都曾设有太学、国子监,更高级的还有翰林院,但都属于官学,与书院是有所区别的。书院一般为民间所办,是士子读书论道的地方。其功能固有应试举业的内容,但亦不尽然,并不全是应试教育,更重要的还是传道,延续道统,既如韩愈所言,吾师道也。因而,在书院里,士子不仅要完成一般的课业,更要研读经传典籍,与老师一起探讨经传的学理和传承。而士大夫不仅以山长、讲师的身份承担着教学的使命,他们往往还是书院的创办者和管理者。这种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传统教学活动,背后隐含着一个深远的意义,也即教育、读书的终极目的,即对人格、人性与文化的塑造,由此对社会人心产生积极的影响,达到社会进步、移风易俗的效果。
由此可见,由士子和士大夫所体现的书院文化,固不同于故宫、天桥、胡同、会馆所承载的文化,既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又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至少书院的创办者都希望通过对士子人格的培养,从而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就是说,士人和士大夫文化事实上构成了传统社会生活中的一股潜流,浸润、滋养着这个社会,使其不至于荒芜和破碎。这个群体,如果不入仕,在民间即为士绅,遂构成社会的基础和中坚。然而,长久以来,我们对于这个群体的思想观念、精神信仰、社会关系、生活方式、习俗礼俗诸多方面都缺少必要的了解,所知也很有限,甚至还有许多误解,以及对他们的污名化。这大约就是在当今的传统文化热中这个群体的文化价值很少得到彰显和认同的原因之一。而通过对书院的关注,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窥视这个群体私密生活的一种方式,从而揭示其文化价值的深刻意义和源远流长的内在原因。
2
书院最早现身于唐代。而北京有书院亦很早。唐末五代时的窦氏书院,是北京书院历史的开创者。尽管我们尚不能确定窦氏书院最初是否创建于北京地区,但创建书院的窦燕山(禹钧)曾在此地生活过,似无异议。窦燕山的名气远远大于他所办的书院,或因《三字经》的广泛传播,“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使他成为与孟母齐名的育儿模范。而他的五个儿子能个个成才,未尝不得益于他所办的窦氏书院。如此看来,窦氏书院或许就是一所具有私塾性质的书馆。但在百业凋零、战乱不息的五代,它的存在,已属不易,如凤毛麟角,亦是十分珍贵和难得的。
继窦氏书院之后,元代的太极书院成为北京书院历史实实在在的起点。它是迄今可考的北京城里的第一所书院。不仅如此,创建于蒙元太宗时期的太极书院,还是元代书院的首创者。它在元大都建成之前,就已存在于北京了。它的最大贡献或意义就在于,伊洛之学即程朱理学由此而传入北方。主讲太极书院的赵复是一位对程朱理学颇有些心得的学者。他是江西德安人,字仁甫,尝家居江汉之上,遂以“江汉”自号,学者称之为“江汉先生”。太子阔出受命伐宋,攻占德安,几十万德安人都成为战俘,赵复就在其中。此时,正在军前行中书省事的杨惟中,与他的合作者,同创太极书院的另一位关键人物姚枢,同“奉诏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辄脱之以归”。赵复因此被杨、姚二人从战俘中解救出来,免于一死。后赵复北上燕都,应聘太极书院,所以说,北方知有程朱理学是从江汉先生即赵复讲学于太极书院开始的。杨惟中、姚枢这些在朝为官的士大夫,听了赵复的演讲,也为程朱理学所折服,并对周、程、张、杨、游、朱等理学家顶礼膜拜。《元史》儒学赵复传就曾写道:“惟中闻复论议,始嗜其学,乃与枢谋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食,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
太极书院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它播撒的程朱理学的种子已在北京地区开花结果。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曾把北方的许衡、刘因和南方的吴澄并称元朝三大儒,其言之曰:“有元之学者,鲁斋(许衡)、静修(刘因)、草庐(吴澄)三人耳。草庐后至,鲁斋、静修,盖元之所藉以立国也。”其中许衡、刘因都出自赵复门下。按照《宋元学案·鲁斋学案》所列师承表显示,赵复名下除许衡、刘因外,还有姚枢、窦默、杨奂、郝经、砚弥坚等,这些人的名下又有自己的学生、门人。从这里起步,程朱理学开始了在元大都,乃至北方的传播历程,可谓枝繁叶茂,代不乏人,子嗣不绝。全祖望说道:“河北之学,传自江汉先生,曰姚枢,曰窦默,曰郝经,而鲁斋其大宗也,元时实赖之。”黄百家亦有言曰:“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诸儒叠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
虽说书院之盛,莫盛于元,然而,元大都所建书院并不多,除了太极书院,见于历史记载的只有房山的文靖书院、昌平的谏议书院和同在昌平的韩祥书院。其中,文靖书院的创办者赵密、贾壤都是刘因的学生,他们创办书院的目的,就是要以刘因的理学教育乡民,从而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他们的书院除了供奉孔子、朱熹等儒家先圣,还供奉老师刘因,立祠祀之。这是程朱理学最早深入北京乡村的实例。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为表彰这家书院尊师重教,不仅取刘因谥号,赐名曰“文靖书院”,还专门为之题写了匾额。至于谏议书院和韩祥书院,由于材料所限,二者的学术倾向和师承传续,都很少为后人所了解,或已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了。
3
说到这里,有个问题是不该回避的,即如何看待辽金统治下北京的文化环境。辽金先后统治北京近三百年。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献于辽,辽升幽州为南京,也称作燕京;后辽被金所灭,海陵王改燕京为中都;二者都把北京作为都城来经营,文化的发生和积累固然有其自身的特点。辽以草原游牧民族进入农耕社会,包括家庭伦理、社会习俗、婚丧礼仪、饮食习惯、文化教育、宗教信仰在内的诸多方面都面临着严峻挑战。掌握辽统治权的契丹贵族既不得不对汉文化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又不甘心被汉文化所同化,儒生士子以及儒学在这里的处境是很尴尬的。《辽史》列传文学有言:“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但其风气刚劲,三面临敌,岁时以蒐狝为务,而典章文物视古犹阙。”话说得很实在。在儒生士子的眼里,辽固为化外之地,儒学不兴,也就不奇怪了。
金人对汉文化的态度与辽则有所不同。统治阶层且不论,士人中,南来北往的,不绝于道。有奉使见留的,也有金取中原后,滞留北方的遗民。他们的汉文化修养很深厚,能诗能文的人很多,这从元好问编纂的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中即可见一斑。该书十卷,收录金朝百年以来二百五十多位诗人的两千余首诗作。元好问本人即一代文宗,“以诗存史”的大家,被誉为具有班、马之才的人物。而郝经在《太极书院记》中亦透露,赵宋南渡后,北方不乏致力于经学的儒士。文中提到的赵秉文、麻九畴,便“自称道学门弟子”。而《金史·文艺》亦有所表示:“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册,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这里虽说泛指北方,而北京固在其中矣。
4
这样看来,仅就书院而言,北京在窦氏书院与太极书院之间是有过长达二百余年的空白期的。也就是说,当书院在两宋蓬勃发展之际,辽、金统治下的北京却如一潭死水,波澜不惊,不曾有过一所书院。直到蒙军灭了金国,建立大元,北京才有了一所可以称誉历史而填补空白的太极书院。这在北京确是破天荒之举,历史上,亦被视为蒙元统治者从武力开国转向文化治国的一个标志。
而且,元朝对书院的政策不是临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稳定人心,维系士心,使社会维持和谐安定的根本性措施。但随着书院在南北各地的大肆推广,则越来越鲜明地表现出一种官学化的倾向。朝廷和各地政府对书院的控制亦明显地加强了。原本书院是作为独立于官学系统,重在私人讲学性质的学术组织,它固然也有为科举提供备选人才的功能,但其主旨还是探求儒学的义理和延续儒家的道统。然而,由于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书院逐渐被纳入官方教育体系之中。
于是我们看到,元代成了书院发展史上的转折点。或者说,元代在书院发展史上划了一道线,前面两宋是书院自由发展的阶段,后面元、明、清是书院日益官学化的时期。而北京书院恰恰是在元、明、清三朝得以发展的。这也是北京书院先天不足之处,没能沐浴到自由发展的雨露。不是说两宋书院没有官学化的倾向,北宋朝廷亦有过振兴官学的努力,而南宋宁宗期间也发生过针对朱熹和道学即理学的“庆元党禁”,朱熹的学说被斥为“伪学”,禁毁六经、四书等书籍,但两宋毕竟是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魏晋之后,又一个思想自由发展的时期,政治、文化政策相当宽松,思想流派纷纷涌现,除了与理学相关的濂、洛、关、闽和邵雍的术数之学外,还有陆象山的心学,以及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孙复、石介等人革新政治的学说和浙江永嘉学者的事功之学。所有这些都要拜书院所赐,宋代学术精神寄托于书院,绝非虚言。
明代延续了元代将书院置于朝廷监管之下的做法。盛朗西引《续文献通考》:“初,太祖因元之旧,洪武元年,立洙泗、尼山二书院,各设山长一人。”这个山长,后改称训导,已非学界名流,而是朝廷官员,拿朝廷的俸禄。永乐皇帝又钦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作为科举考试的统一教材,并在北京增设国子监。士子读书因而受限,遂造成书院讲学之风的衰落和士子的贫血症。盛朗西曾有言:“宋元之间,书院最盛,至明而寖衰。盖国家网罗人才,士之散处书院者,皆聚之于两雍,虽有书院,其风不盛。”两雍即国学、官学的代称。这是明初的情形,并延续了百年之久。直到嘉靖年间,北京才有了建于延庆居庸关的叠翠书院。
有明以来,这里一直都是防御蒙古骑兵侵扰的前线,大批军人驻守于此。为了给守边军人的子弟提供一个读书场所,监察御史萧祥曜借居庸关旧有之泰安寺,稍加修葺,改建为书院。而明中叶以后书院的复兴,则与王阳明、湛若水创建学派,聚徒讲学互为因果。犹如伊洛在北宋、朱熹在南宋,都曾被朝廷以伪学申禁一样,王阳明、湛若水亦曾被廷臣指斥为邪学,嘉靖皇帝亦有禁毁书院之举。但作用不大,书院讲学之风虽一时受挫,却并不稍辍。及至万历朝,张居正当国,他痛恨书院讲学,意欲遍撤天下书院,亦未能奏效。而东林书院领风气之先,使书院讲学之风大盛,仅在北京,嘉靖、万历间就建有叠翠书院、通惠书院、杨行中书院、白檀书院、后卫书院、闻道书院、双鹤书院和首善书院。其中闻道书院和首善书院都因牵扯到东林而见忤于朝廷,痛遭噩运。特别是首善书院,既建于京师之内,而主持清议,议论风生,却不幸困于党争,终以东林的名义,毁于魏忠贤之手,成为阉党尽毁天下书院的牺牲品。
5
清朝皇帝对书院的态度也表现得很纠结。可以想象的是,清初当权者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局面。南明政权仍在南方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斗争,以图复国;而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也在南北转战,并有联明抗清之势;再有就是很多士人对异族新政权并不认同,表现出一种不合作、不入仕的态度。他们大多延续明末书院讲学的方式,表达其精神所寄和学术根柢。这是清初当权者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形。他们既认为书院讲学导致了明朝的败亡,自然担心以东林为代表的自由讲学、清议朝政、臧否人物、互结党援的流风余韵浸淫于新朝。因此,他们早期采取抑制书院的做法,强化对书院的控制。《清会典》即明言:“凡书院义学,令地方官稽查焉。”
但有着数百年历史传承的书院在教民育人方面确有官学所不能替代的优势。因此,在社会政治危机趋于缓和之后,清廷势必要放宽书院政策,康熙皇帝曾给很多书院赐书赐额,就显示了朝廷对书院的关怀和支持。北京金台书院的前身大兴义学就曾得到过康熙皇帝所赐御书“广育群才”。但朝廷对书院的管理并未放松,雍正、乾隆一直强调挑选书院管理者的标准,即政治上要可靠,德行要高尚,学识要优秀,目的是在笼络人心的同时又防止书院滑向明末清议朝政之路,从源头上阻断明遗民利用书院反清的一切可能,将书院疏导引入当权者设计的发展轨道。清代书院政策之有效,也因为康、雍、乾三朝之文字狱的配合。思想既不自由,遂影响到士人的治学和讲学。宋明学者都有不为相则为师,得君行道,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和情怀,由明入清的学者最初或仍抱此理想,但乾隆一句“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尤大不可”,便把清代学者打入故纸堆中。虽然梁启超把汉学在民间的兴起,看作是对朝廷提倡程朱理学的一种抵抗和反动,但学者乃以论政为大戒,钳口不敢吐一言,亦是事实。于是,清代书院要生存只剩下三种可能:“一为讲求理学之书院,一为考试时文之书院,一为博习经史词章之书院。”
6
书院的兴衰优劣,需要许多条件,有硬件,如校舍、田产、资金,也有软件,如山长和讲师;有外部因素,朝廷政策、社会环境、地理位置,也有内部原因,如办事人的学养、素养。这些都可能影响到书院的追求和品位,并进而影响当地的士风、民风,也为当地文化的建构提供相应的资源。
就清代北京书院的局限而言,首先就在于北京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作为元、明、清三朝的都城,不能不影响到北京书院的生存和发展方向。一方面,可以享受到京师作为首善之地的优越性,既在天子脚下,朝廷身边,阳光雨露随时都可能恩赐于某一所书院,金台、潞河都有过切实的感受,它们都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过官家、朝廷,乃至皇帝的关怀和资助。但它们也很难像理想中的岳麓、东林、白鹿洞、嵩阳、关中书院那样,办成以名家讲学相标榜的书院;更不能像王阳明、阮元、张之洞那样,为自己的学术理想和主张办一所书院;甚至做不到像京外的莲池书院那样,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和主张。北京的书院大多表现为一种庸常的状态,很少表现出特立独行的风格。即使是所谓官学化,也与外省有所不同,并不以道学或理学为重,而是以科考、时文为重。
当然,也不能说北京书院没有过儒学大家和学术领袖。元代的太极书院就有过赵复、杨惟中、姚枢、郝经、刘因、许衡等硕儒;明代的首善书院也聚集了冯从吾、高攀龙、邹元标等一班名流;而马经纶的闻道书院,亦有李贽加盟,在易学研究方面有过卓越贡献。即使在清代,主讲金台书院的亦有王昆绳、陈木斋、陈句山、顾虞东、姚汝金诸先生;潞河书院则有理学名臣张伯行,清代有三人本朝官员从祀孔庙,他是其中之一;还有擅长经史校勘的张云章,以及学行俱佳的董元度、诗人李调元和财政学家王茂阴等;做过同、光两代帝师的翁同龢,也曾主讲过昌平的燕平书院。尽管如此,北京书院整体上仍为舍讲学而尚考课,常常是由山长课题,或者由地方官员课题,除了岁考,还有月考,每月一考,或数月一考,目的就在于训练生徒以应付科举考试。
7
北京的书院,只有三所开办在都城之内,即元代的太极书院,在金中都内;明代的首善书院,在宣武门内;清代的金台书院,在前门外金鱼池;其余的,都建在城郊州县。这种现象为我们思考书院在厚民风,兴教化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历史上,国人的教育是由儒家负责的。儒的最初职业就与教育相关。儒学的开创者孔夫子,终其一生,都以教书育人为职业,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按照儒家所想象的上古三代的盛况,曾有一位名叫“契”的人教以人伦,后经孟子概括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因此,后世无论官学还是书院,都把化民成俗视为终极目标。像元代的赵密、贾壤,先是受教于容城刘因,后回到家乡房山,创办文靖书院,特别标榜其办学目的为“欲一乡兴起为善之心焉”。如果我们考虑到元初房山一代的乡风民俗,就不难看出书院创办者在此传播程朱理学的用心之良苦,颇有点孟子所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的味道。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对州县地方官员表示一种敬意。这些人创办书院的动机,多数是为了履行为官的责任和义务。他们为官一任,施政一方,无不想为地方做些有益的事,常常是下车伊始,先拜孔圣人,再考察学校、书院,见到书院倾圮毁坏,便捐俸修建。但通常他们都是“飞鸽”牌,而非“永久”牌,知一州、知一县的时间都不会很长,有时书院刚刚建成或尚未建成,他们就转迁别处去了。这也是北京书院难有更大作为的原因之一。不过,他们努力办学的结果,常常是把学者看重的道学、理学、儒学,简化为人人可以理解的伦理规范,传至民间。儒学能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他们是传播中的最后一棒。他们创办书院最看重两个方面,一是移风易俗,教化民众,一是明经取士,为国选才,故有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豪迈。而说到底,二者在儒家的教育理念中其实是一回事,或曰一事而两面。前者讲的是,受到“明伦”教育的士君子,以德化人,通过自身的表率作用,推己及人,造福乡里,形成知书达礼的乡风。这或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濡染熏陶的过程,难收立竿见影之效。而后者讲的就是如何造就一个明义理,修其德,心系天下苍生,具有先忧后乐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士君子。而化民成俗就内化为他们的使命。他们也许未有陆九渊、朱熹在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但其思想和作为,还是会影响到当地的士风学风、民气民俗。北京何以称为首善,不仅仅源自它的政治地位,更来自历史上州县办学所涵养的民间的读书风气。所以说,首善之善,惟在读书。
8
书院的命运终结于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北京的书院亦如是。而书院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受到质疑,首先是由于科举制度、八股时文的牵连。大清帝国在与西方列强对抗中一败再败,西方学术文化借坚船利炮的优势席卷中国,于是,几乎所有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都意识到了这种危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就有专章讲到如何培养造就、发现选择国家急需的有用之才。而科举最大的问题,即“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
朝廷内也有官员发出变法改革的声音。继顺天府尹胡燏棻上疏要求把省会书院改制为学堂,变法自强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亦奏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一折,提议有步骤地将各地书院改为学堂。戊戌变法期间,改书院为学堂更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康有为奏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把西方列强的兴起归结为国民教育的普及,因而提出:“奏为请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令小民六岁皆入学,以广教育,以成人才。”光绪皇帝随即颁布了《改书院为学校上谕》,可惜,戊戌变法不久即因慈禧政变而告失败,书院改为学校一事亦被叫停。直到两年后,在庚子事变和辛丑条约的巨大压力下,慈禧启动新政,各地书院才陆续改为学校。
其实,在变法进行中,就有稳健派官员和学者表示过担忧和疑虑。曾经主持保定莲池书院的吴汝纶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表达了“务求实效,不在欲速”的看法。但在历史大潮的裹挟下,稳健、保守的声音总是显得很微弱,常常被湮没在激进的、理想主义的喧嚣中。而靠行政命令,整齐划一,一刀切完成的改革,虽然看上去很美,却很容易留下后患。多年后,胡适在《书院制史略》中就谈到:“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唯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
虽然如此,书院精神惜未绝迹。谢国桢作《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就曾提到:“自光绪之季,放(仿)效欧西,创立学校,垂三四十年,其间学制,迭有变更,卓识之士,渐知学校功课庞杂,且过于机械,一人之智力有限,难以精工,是以学鲜专门,士乏良识,是吾国学界之一大缺点也。乃仿英国大学之制,及昔日书院之设,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学爰有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学校有研究院之设。使学子得有专门之研究,思想有自由之发展,晚近吾国虽忧患频仍,学术则不无进步,是均梁任公、蔡孑民诸先生提倡之功,而研究院之制度,则犹具书院之雏形焉。”这样看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和清华大学研究院,或者倒是北京书院的余绪啊!
供稿: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