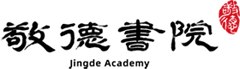刘云春丨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论纳兰词之真
清词中兴,词家济济有众。叶恭绰编选的《全清词钞》收录作者逾三千,纳兰容若就是其中最杰出的词家代表。近代词论家况周颐(1859—1926)盛赞纳兰为“国初第一词人”;王国维(1877—1927)以境界论词,指出“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王国维《人间词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纳兰词之真,在于其未染“汉人风气”。至于何种汉人风气,王国维并没有深入辨析。从纳兰所编选的《通志堂集》诗文中可知汉人风气是指清初词坛好复古、事雕琢的风气。纳兰容若与陈维崧、朱彝尊并称为清初三大词人,却不属于任何词派学宗,孑然独立。浙西派朱彝尊(1629—1709)词婉丽,自比南宋张炎,标举姜白石清空雅骚之词风。阳羡派陈维崧(1625—1682)学苏、辛词之豪雄。对于这种以南宋词为宗的词学风气王国维予以了辩驳。他在《人间词话》中认为姜白石的词格调过高,不在境界上用力,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不入第一流作者之列。而学辛弃疾词者则多学其粗犷滑稽,不懂“幼安佳处,在真性情、真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1页)关于复古与创格的关系,纳兰容若以孩提与乳母的关系作喻,认为婴孩不能没有乳母,但又不能一生在乳母胸前度日。诗人学习模仿古人后必须学会独立门户、自成一格。纳兰性德反对昌黎逞才、子瞻逞学,因为那是于性情隔绝的作诗之法。他明确提出“诗乃心声,性情之事也”的诗学主张,走上了抒性灵、写至情的美学风格。(黄天骥《纳兰性德和他的词》,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58页) 纳兰词之自然真切,主要有以下三点诗学特征。 其一,不作闺音,不写艳词。词本属歌体,初为歌馆教坊名优演唱娱众之辞。词客与伶工身份的错位,决定了早期词中叙写声音的自我戏剧化。男性词人在词中叙写的双性心态,形成了花间范式的词学美感。“男子做闺音”的传统,多表现在宫怨体诗中,男性词客文人代女性设辞、假托女性身份与口吻咏物抒情。这类词多表现男子对于女性的玩赏与欲求,往往不免流为淫亵及轻薄。这种传统到了苏轼那里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东坡词里的女性即使是歌姬侍女,也不再是可供爱悦消费的“他者”,而往往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与人格的个体。这就是词的东坡范式。宫怨体词在清初不再盛行,原因有二:一是顺、康两朝后宫体制改革,宫廷中宫女不多,宫怨体诗歌产生的社会背景已经基本消失。(施议对编选《纳兰性德集》,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21页)二是词体文学以感性抒情为本的诗学理念已经渐入人心。在《填词》一诗里纳兰对花间范式艳词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为多写秦楼楚馆、风花雪月的花间欢愉之词对社会裨益不多,也是导致元明两代词体文学衰微不振的原因。词应写性情中事,词人应该有屈原、杜甫那样的忧患之思。纳兰不以宫怨词为主,也不作花间艳词,而是以本我声音出现在词中,把个人的生命体验升华成普遍的人性情感与美感。 其二,抒情写忧的情真。康熙十六年,纳兰与著名词人顾贞观以“抒情写忧”的主要标准合力编选了《今词初集》两卷,纂录清初词家184人的作品。“抒情写忧”也是他的创作理念。《纳兰词》共342首,总是以一个深情的恋人、钟情的丈夫和真挚的友人身份出现,一改“男子作闺音”的代言传统。清词里宫怨虽不是主流,但男性词人以真实的性别与社会身份——失恋的男子、悼念亡妻的痴汉、性命相见的友人出现在词里,也并不普遍。《画堂春》“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中恋人的声音直露热烈,几乎喊出了爱的誓词:“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忘贫”。纳兰与江南词人顾贞观(1637—1714)之间的莫逆之交已成清代词史上的佳话。如《金缕曲·赠梁汾》中“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的至深友情,实在是袒露襟抱的咏怀典范。纳兰怀念妻子的悼亡诗不少,尤见情深,如《青衫湿·悼亡》开篇直抒胸臆,“近来无限伤心事,谁与话长更?”,哀婉凄切。词尾“忽疑君到,漆灯风毡,痴数春星”以白描手法刻画了春夜繁星下思念亡妻的痴汉形象。纳兰短暂的三十一年生命中,曾先后七次扈从康熙帝出巡大江南北。这种阅历扩大了词人的视野,也提升了其词的境界。纳兰的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中的“夜深千帐灯”与《如梦令》中的“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的新颖豪壮,被王国维称为“千古壮观”的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7页)。纳兰也有不少历史忧患之作。游览历史名胜,也激发了纳兰作为文人志士的千古幽怀,如《南乡子》“霸业等闲休,跃马横戈总白头,莫把韶华轻换了,封侯。多少英雄只废丘”的历史兴亡慨叹,颇有南唐后主词的悲切深沉。王国维说词到李后主才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纳兰词不仅追南唐后主的“烟水迷离之致”,也还有作为中国传统士大夫词人的眼界和深邃。正如别林斯基所论:“伟大的诗人谈着我的时候,就是谈论这普遍的事物,谈着人类。因为他的天性里就存在者人类所感受的东西。” 其三,词调表情丰富,修辞直言无隐。纳兰三百四十多首词,选用词调多有近百种,除了常见的《忆江南》《浣溪沙》《清平乐》《菩萨蛮》《蝶恋花》外,还有《河传》《荷叶杯》《太常引》《赤枣子》《茶瓶儿》等不常见的词调。其中只填一首词的词调占到了一半。词本为音乐文学,每一种词调的格律、声情、体制都不同。每个词调的句式组合,奇偶句的韵位疏密,平仄与换韵,与表达情感的喜悦、忧愁、悲哀、热烈、愤激、缠绵、疏快、旷达、豪放、柔婉都有紧密关系。《纳兰词》词调的多样性,足见其词表情的恰切、丰富与细腻。如《长相思》本为乐府古题,多用于抒写男女相思主题。该调用平韵,表情流畅而热烈。纳兰以此词调写羁旅游子风雨兼程的苦楚以及对乡关故园的渴盼之情。上片“山一程,水一程”与下片“风一更,雪一更”两相呼应,塞外大漠风光与游子的思乡柔情刚柔相济,相映成趣,堪为经典。 纳兰词的修辞往往直言无隐,多在词首和词尾用问句来破题或收束。词首与词尾是词的修辞要害处。问句开篇,往往显得毫无心机,直陈心迹,真诚无伪。如《荷叶杯》开篇“知己一人谁是?”,又如《临江仙·寒柳》“飞絮飞花何处是?”词尾以问句收束,往往使词言简意长,意味无穷。比如多首《忆江南》调中便有“谁在木兰船?”“还似梦游非?”“谁与话清凉?”。传统词家都重视结句的重要性,南宋张炎就曾说到作词比作令曲更难,就像诗歌里的绝句最难写一样。一首词仅十来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有余不尽之意最好。纳兰词喜用问句的修辞明显是继承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体美学。“李煜却解放了这种美学教条,开始把疑问句置于句首,期能吸引读者注意他的感情强度——虽然他同时也保存了基本技巧,在词尾制造微言大义。”([美]孙康宜《词与文类研究》,李奭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8页)这种言外之意、深微幽隐之美正是王国维所谓词体的“要眇宜修”,叶嘉莹所谓词的“弱德之美”。凡被词评家称为低回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好词,其美感品质都属于一种弱德之美。(叶嘉莹《弱德之美:谈词的美感特质》,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61页)若论词人纤美善感的心性以及词体深微幽隐的弱德之美,纳兰都兼美一身。 纳兰容若承平少年,乌衣公子,天分绝高。其词一改“男子作闺音”的传统,“纯任性灵,纤尘不染”(况周颐《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121页)。可惜他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最终没能胜任清词的“起衰之任”。纳兰词雄视元、明两代,甚至越过苏、辛之词,直追南唐后主词抒情感性本体,终成“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大词家。朱祖谋(1857—1931)“清词的境界独到开拓之处,连宋人也未必能及”的说法是有一定学理性依据的。 (作者:刘云春,系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供稿: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