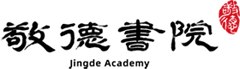鹅湖书院:自古乾坤为此理
透过“道学之宗”匾额下的红漆木门望进去,两盏古朴宫灯各擎一朵暖光,静垂于“讲堂”檐下。一株枫树举着红黄纷披的叶子,高大的柚树将浑圆的柚实悬挂其上。岁月的苔痕布染于台阶与青砖地面,两三朵兰花绽放在幽静处。讲堂无疑是一座书院的核心之处,一场场考试,一次次升堂讲说,一轮轮答疑辩难,都像一次次有力的“心跳”,将生机勃勃的思想汁液注入士子学人的精神血脉,亦成为一座书院生气勃勃的源泉。
讲堂内悬挂着《朱子教条》,被无数后学奉为圭臬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言忠信,行笃敬”“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门前红柱上一副对联:“自古乾坤为此理,至今山水有余光。”数百年前曾闪烁于这片山林的思辨的光芒,至今未曾黯淡。
空气中氤氲着恍如暖春般的气息。我们走进鹅湖书院,穿过嵌有“鹅湖书院”“圣域贤关”的西大门,穿过高举着“敦化育才”匾额的头门,穿过环饰翘飞的鲤鱼尾和龙门图形的石牌坊,穿过挂有“既有学规传白鹿,可无泮水育红鹅”对联的仪门,穿过青石桥中分的半月形泮池,细瞧静观间,忽闻一阵喧声。驻足回看,一群穿着校服的孩子奔上状元桥,穿过泮池分散于书院各处。有的手中拿一纸,走近细看,原来是研学的“打卡表”。一道道门槛,一处处回廊,一间间士子号舍,顿时被孩子们的声音充满,正应了讲堂内一联“鱼跃鸢飞斯道由来活泼泼”。
中国历史上有书院7000余座,江西一省就有千座,鹅湖书院何以在众多书院中脱颖而出,跻身“四大书院”之列?便与这“活泼泼”的学术精神与生态,与其标举的求真问道的执着态度有关。

明景泰年间,大理寺少卿李奎在《重建鹅湖书院记》中写道:“大江以西,古称文献之邦,书院之建,不知有几?惟鹅湖之名与白鹿并称于天下。”明代进士、曾任国子监五经博士的吴世良则认为,“天下四大书院:嵩阳、岳麓、白鹿洞、鹅湖”。鹅湖书院是少有的先有神、后具形的书院。古来著名的两度“鹅湖之会”,其实都发生在鹅湖书院建立之前。
公元1175年夏天,鹅湖山迎来一群衣袂飘飘的身影,其中有吕祖谦与朱熹两位大儒。两人已在福建盘桓一个多月,朝夕切磋,共读了北宋理学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的著作,由衷感叹先贤“广大宏博,若无津涯”,摘编诸子著作精华编成《近思录》作为理学入门教材。或许是在切磋和编著过程中,吕祖谦萌生了调和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理论分歧,使之“会归于一”的念头。
这年的农历五月十六日,两人从寒泉精舍动身,前往信州铅山鹅湖寺(今江西省上饶市铅山鹅湖书院),路上不疾不徐而行,如磁石吸铁,沿途会聚而来的士子学人越来越多。到鹅湖山不久,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也应约而至。吕祖谦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谈及这一场“鹅湖之会”:“与朱元晦相聚四十余日,复同至鹅湖,二陆及子澄诸兄皆集,其有讲论之益。”
“会者百人。云雾聚,一何盛也。”(明代郑以伟《游鹅湖及诸洞记》)众人齐聚鹅湖寺,朱熹与二陆各执一端,连辩三日。陆九渊认为“吾心千古不磨”,人性本善,养好“本心”自然能感知万事万物,见性明理,其理论源头可追溯至孟子的“良知良能”说。而朱子主张“穷理居敬”。今日鹅湖书院泮池边的碑亭里尚存一碑,上刻康熙年间巡抚江西的白潢对“穷理居敬”四字的解读:“穷理居敬一言,尤学者所宜详玩焉。河南夫子所谓或读书以讲明义理,或尚友以鉴别是非,或应事接物以审量当否,皆格物以穷理之事也。敬者,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也。敬,德之聚也。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静时不敬,则昏迷纷扰,无以立天下之大本;动时不敬,则懈慢放肆,无以行天下之达道。故学以居敬为基……”
二陆与朱熹从各自的哲学观点出发,提倡不同的治学方法。二陆强调本心自足不假外求,养心、修心为大;朱熹则强调格物致知,穷尽天下之理,方能明心见性。此所谓中国理学史上的“遵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双方都注重学术理性,崇尚“求真”,鹅湖开辩后,气氛如绷紧之弦,双方侃侃而谈,不肯退让。及至陆九渊吟出一诗,中有“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意指朱熹探求学问的方法乃“支离事业”,耽于琐细,朱熹听之顿然失色,拂袖而去。
鹅湖山中的这一场辩论,惊动天下学人,关乎学术,关乎理性之思,关乎为学求道之径,也关乎人生选择与政治理想。激辩三日,虽然未能如吕祖谦所愿“会归于一”,但鹅湖山道成了千千万万求真问道之径中著名的一条。二陆的“心学”从这以后广为天下知,而朱熹在鹅湖之会后坚定其志,潜心完成《四书集注》,奠实一代大儒的地位。他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数百年间众多书院秉持的教育准绳,使得以书院为载体的教育体系更趋规范完善。
朱子门徒徐子融、陈文蔚接续在鹅湖寺旁建茅屋,聚徒讲学,“以斯文自任”。后人在讲学之地旁设“四贤祠”,以纪念鹅湖山历史上、亦是中国文化史上那一光彩焕然的时刻,与那一时刻中挺立的四位贤士的身姿。
另一场著名的“鹅湖之会”,发生在13年后。
公元1188年冬,漫山大雪冰封了鹅湖山道,两位热血青年破冰踏雪而来,走进了寂静的鹅湖寺。他们是辛弃疾和陈亮。天地冰寒,却无法冰冻滚烫的热血与内心的热望。这一年,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再次上书朝廷,请求恢复中原,建言用“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他心中的“非常之人”,就有辛弃疾与朱熹。上书没有回应,只落得朝臣讥笑。心中郁郁的陈亮,邀约辛弃疾与朱熹促膝相谈,共商抗金复国大计。辛弃疾应约而来,两人惺惺相惜,“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并肩漫步于鹅湖山林中,酒入衷肠化作一把热泪。苦等多日,朱熹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在山道上,两人只能怅然作别。陈亮不知,此时的朱熹已收束一心专注学术。
与陈亮作别后,辛弃疾内心无法平静,行至半途情不自禁调转脚步追赶陈亮。追至鹭鸶林中,雪淤污泥深,前路空茫不见人,他只得颓然驻足。难以释怀的辛弃疾行至方村,深夜独酌,神思恍惚之际,忽听得一线清亮的笛音穿透沉沉夜色。这清音催动他的满腹悲愤,遂提笔写下《贺新郎·把酒长亭说》:“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长夜笛,莫吹裂。”一腔滚烫的英雄泪,随笛音抛洒。
吕祖谦选择鹅湖山,想来不是偶然。陈亮选择鹅湖山,更是慎重之选。鹅湖山是武夷山脉的一条支脉,“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唐诗人王驾《社日》)。这座叠翠藏珍的山林因历史赋予的人文光华,成为士子学人心中一处重要的文化地标。淳祐十年(1250),南宋朝廷为鹅湖四贤祠赐额“文宗书院”。明景泰年间,文宗书院正式更名为鹅湖书院。近800年间,鹅湖书院成为诸多名士路过或取道铅山时,必会慕名拜访之地,因而留下了诸多诗词、对联、文章与墨宝。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爱新觉罗·玄烨亲书“穷理居敬”额与“章岩月朗中天镜,石井波分太极泉”联,赐鹅湖书院悬挂。
跟随孩子们的脚步,我走进“讲堂”,两边墙壁上4个端穆的大字“忠、孝、廉、节”,来自朱熹的谆谆教诲。走进一代代学子求学问道的号舍,仿佛看见他们在这里捧卷夜读,相互问答,与山人、讲师辩疑,以探索真知、提升自身修养为归旨,并不一心为科举应试。他们如涓滴之水,汇入中国知识分子共同构建起的生生不息的精神长河,汇入绵延数百年“活泼泼”的书院文化。萌芽于唐,蓬勃并完善于宋、明、清三朝的书院文化,以尊重个性差异、重视学生主体性的教学方法,涵盖哲学、教育、历史、地理、经济、管理、文学、美学、伦理学、建筑、文物、图书馆学、宗教等众多学科,其中积淀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与众多书院一样,鹅湖书院几度迁移、损毁,却总有富有见识的地方官吏、士绅、饱学之士倾力将之修葺,不断筹资充实书院藏书,使之至今挺立在鹅湖山中,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日月轮回间迎来一拨拨心慕先贤、潜心研学的学子。
朱熹强调通过格物致知把握真理,思想承续正统又有自己的创见,他一生著述丰厚,为书院讲学立规,影响无数后学;陆家心学讲求通过内心澄明直见道体,独树一帜,陆九渊登上国学讲台讲《春秋》;辛弃疾一生怀抱抗金复国之志,晚年归隐山林湖畔,于诗词中徘徊咏叹,“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无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走在寻求自我生命完善与实现人生理想抱负的路上。虽受时代所限,他们的思想与言行亦带有自身的局限性,但800多年前,这几位史册留名的大家,以自己的精神之光照亮了鹅湖山的山林丛莽,使之在中国文化地图上成为一处鲜明的标识,那光亮亦照亮了无数后学的学术与精神探索之路,熠熠,常新。
供稿: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