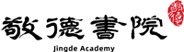屏风:一种礼仪文化的重要角色
在古代,屏风不仅是一件室内的古典家具,也是一种礼仪文化的重要角色。在几千年的历史流转中,它曾是帝王权力的象征,是教谕世人的明镜,也是中国书画创作的独特媒介,还寄托了古人闲情逸致、追求理想生活的美好愿景。
清代 彩刻汉宫春晓花鸟十二扇屏风局部
历史中的屏风形象
屏风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并不叫屏风,而是一种称为“斧扆”(又叫作斧依、黼依)形似屏风的帝王专用器具。“斧”指的是屏风上面斧头的纹理,黑白相间;“扆”则是一个地点。《仪礼·觐见》曾提到:“天子设斧依与户牖之间,左右几。天子衮冕,负斧依。”西周初期,屏风是古代政治活动中的必备之物。在一整套礼器组成大型礼仪场合里,天子站于屏风之前,向南朝向群臣,塑造一种庄严、肃穆之感。
屏,遮蔽之意,屏风既是遮蔽物,又是一种遮蔽行为。天子位于屏风之前,向外宣示身份地位;位于屏风之后,保持神秘感,令人心生畏惧。通过视觉上的遮蔽和隔断,营造这个空间里天子居于高位的统摄感。
另外,郑玄在注《礼仪》中写到:“天子以屏风设于扆,诸侯无屏风”,说明屏风是天子专属物,只有当时的天子可以使用。随着后世礼仪和屏风形制发生了变化,屏风逐渐成为一件百姓日常生活的家具。不过,“天子立于屏”这个王权象征未曾改变。比如,《明穆宗像》中,皇帝处于正中央,背后是“山字式”座屏,左右两侧装饰着腾空而起的巨龙,以此体现九五至尊的地位。在故宫的太和殿中,我们依然可以见到布满金龙的御座立屏。
从汉代开始,屏风的实用功能开始显现,种类和形制变得多样化。除了座屏,还出现了独扇屏、枕屏和多扇组成的曲屏。曲屏也叫作围屏、连屏或叠扇屏,常常与床榻、茵褥结合使用。汉代沿用了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床榻和茵褥成了就寝场所。曲屏不仅有挡风避寒、分隔空间的实用功能,还是王侯世族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
从东汉至唐代以来,造纸和丝织技术的发展为屏风提供了丰富的材质,衍生出多种用途。在唐朝时期,屏风形制上出现了大型的地屏,可以挡风避寒,还能重新分配室内空间,起到私密隔断的作用。还有在围屏基础上改良的折屏,分为四、六、八和十二等式样,每扇屏芯可以用来书画创作。当时的唐代名家在屏风上绘画和题字成为了一种潮流,山水画屏和仕女屏风盛行一时,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
到了两宋时期,由席地而坐的低矮家具转变为垂足而坐的高型家具,形制小巧精致的枕屏、床屏和砚屏发展至高峰。屏芯材料还采用大理石、天然云石,纹路肌理好似山水画。宋代的文人意识进入绘画艺术,崇尚自然的造物观和追求恬淡雅致的审美观影响了家具设计与制作,带有文人风尚的屏风成为宋代美学的独特标志。宋代文人的山水画屏讲究神韵和意境,映照了文人的精神世界与内心情感,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雅趣和美好憧憬。
到了明清时期,屏风的材质和装饰工艺将屏风艺术推向了鼎盛。明代屏风用料非常讲究,多用红木、紫檀、黄花梨等名贵木料,雕刻花鸟、山水、人物和书法题字,加之镶嵌名贵石材。屏风的装饰手法更为丰富多样,常用雕刻、镶嵌和彩漆等,还出现了一种悬挂在墙上用于室内装饰的挂屏。清代屏风沿袭了明代工艺,受宫廷文化的影响,屏风的造型更加厚重,装饰工艺更加繁复,形成了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风格。从装饰工艺上来说,清代的屏风艺术到达了历史巅峰时期,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比如罕见存留的清康熙款《彩刻汉宫春晓花鸟十二扇屏风》,历经三百多年品相完好,是难得一见的传世珍品。
屏风伴随着中国历史发展,有过辉煌时期,也曾盛极而衰,走向没落。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实物载体,有着鲜明的历史烙印和审美变化。现在,作为一种纯艺术品装裱形制的屏风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它成为了一件实用美观的家具或家具装饰品。但是,屏风艺术的魅力穿越了历史,给予我们认识古人生活起居、礼仪文化和古典艺术的独特视角,感受到人与器物空间之间的深远关系。
周文矩《重屏会棋图》
屏风的东方美学意象
汉代以后,屏风开始以“画中画”形式出现,是中国绘画中用来构造空间的特殊符号之一。艺术史家巫鸿在著作《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中提到“作为一种准建筑形式,通过表面装饰的屏风图像,成为了一幅幅‘画中画’实施着为画中人物赋予个性的隐喻功能”。其中,比较典型的《韩熙载夜宴图》、《重屏会棋图》和《勘书图》,这三幅绘画作品中的屏风作为了关键的视觉隐喻。
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是一幅长达3米多的叙事性手卷,由“演奏、观舞、宴间休息、清吹、欢送宾客”五个场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视觉之旅。画中屏风将每个场景划分为独立单元,是情景叙事的连接点,又巧妙地完成了时空转换。屏风的对称性构图既强化了画面的深度感,又作为隐蔽和敞开的分界点,提供了一重较为隐晦的窥视欲。
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在作品中同时出现了仕女屏风与山水屏风两种屏风样式,引出了独特的“重屏”构图。画面描绘的是南唐中主李璟和他的三位弟弟一起下棋,身边站一童子。屏风中夫人和仕女在侍寝主人,在床榻后面是一扇山水屏风。这种双重屏风建构的空间感,逐步引导观者的视线走向纵深,产生了一种混淆真实的观感。此处,借由重屏的幻境隐喻了权力与隐退的主题。
在王齐翰的《勘书图》中,最醒目的主体是一扇几乎横贯整个画面的山水屏风,中间是烟云飘渺的山水景象,高山脚下、平原之上有一处屋舍。主人公位于屏风的右侧,正在“怡然自得挑耳朵”,展现了他不拘小节、悠闲小憩的生活场面。这扇硕大的屏风就成了一个远方的风景,代表了文人追求林泉高致的心像符号,隐喻了主人公向往隐居山林的理想生活。
屏风的美不仅在于本身的装饰和形制,还体现在它作为一种轻质灵活的隔断物,在空间设计中成为了一种装饰美学。它的遮蔽和隔断功能对应着中国建筑艺术隐与露的空间意境。屏风可以根据空间陈设、功能需求和人的心情变化进行折叠伸缩,灵活移动,造成隔而不断,隔而不堵,在半遮半掩中给人以遐想空间。特别像丝绢、丝帛这类半透明材质的屏风,具有似隔非隔、似空非空,虚实相生的视觉效果。
另外,屏风作为一种情景媒介与周围环境融合在一起就成了一种特别的景致,姿态多变,光影随行,动静结合。如唐代杜牧所作“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李商隐诗中“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屏风与人在浮光掠影间产生了一种朦胧美。
屏风的表面也成为了一个诗意的空间,经常作为古人诗歌的表现对象。诗人将屏风的美学用诗词的形式来展现,不论是描绘屏风画面的意境,还是刻画空间环境的氛围,都能引发读者的无限想象,影响着后世对屏风美学的创作。当然,屏风亦是文人士大夫寄情托志的特殊载体。白居易就在居所与素屏为伴,写过许多自己与屏风的生活关系,譬如《素屏谣》中“吾不加一点一画于其上,欲而保真而全白。”借素屏来表达自己不追求名利,保持全真、宁静的人生态度。在晚年所作的《卯饮》中“短屏风掩卧床头、世间何事不悠悠”描写自己闲暇小酌后卧在床屏上的惬意状态,展现了一种逍遥自在的文人生活。这也常常被后世作为一种可以入诗、绘于画上的理想状态。
屏风所蕴含的精神文化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逐渐形成,早期的屏风是一种礼器文化,作为帝王权力的象征,在大型礼仪场合下营造一种威仪感。在人们的意识中植入一种至高无上的政治秩序,用以维护统治阶级地位。到了汉代,它作为“鉴戒屏风”,承担了训诫内省的教化功能。屏风表面常绘制古代圣贤人物故事,放在君主的日常起居中提醒君主以此为鉴,表面的图文形式还有助于直观方便地教化宫廷女性,宣扬美好品德。
魏晋时期,儒、释、道融合,组成了古人的精神文化,宗教题材在中国绘画艺术中兴起,在屏风绘画上也表现出清新秀美、婉约飘逸的浪漫主义风格。到了唐代,屏风已然走入寻常百姓之家,屏风绘画的主题更加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花鸟、山水、人物、诗书等形式使其更富有诗意,表达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直到两宋时期,屏风的文化功能从警世教谕的说教意味真正转向了文人精神的代表,更强调一种器物美学与精神气质的契合。人们在屏风上作画题字既是一种美的装饰,也是情志意趣的表达。山水屏风成为了文人日常活动的背景,在宋代的绘画作品中常见自然山水与山水屏风相融合,文人雅士在真实与虚拟的山水空间里互动,有一种独特的意境之美。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到了这种文人的山水愿景,“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绝断”。文人士大夫在一方山水画屏里,抛开世俗杂念,去神游心中的精神世界。
屏风,作为东方古典美学中的一个意象,在隔而不断、露却不尽、半遮半掩之间体现了一种“含蓄美”。有诗言“屏风有意障明月,灯火无情照独眠”,它既是人们的起居器物,也是形而上的文化符号。
作者:陈孟伟(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讲师)
供稿: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