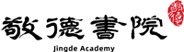王雪梅:祭之在祠:祠堂空间的圣与俗——以朱子《家礼》为中心
摘 要:朱熹编撰《家礼》,希望将儒家的礼仪能够全面贯彻到士庶的生活世界。《家礼》创设祠堂制度,祠堂成为士庶举行礼仪的圣凡空间。透过《家礼》,可见朱熹礼仪世界的神圣维度:祭之在祠、祭之在时、祭之以物、祭之以诚共同构建了祠堂为中心的神圣空间;同时,在祠堂举行的冠、婚、丧人生礼仪以及日常礼仪则显示了祠堂作为凡俗空间的面相。通过仪式的践行与仪式的转换,儒家礼仪与日常生活结合,圣与俗在祠堂空间实现了共融。除了宗法现实的目标外,朱熹为士庶构建了儒家正统生活下的神圣世界,建构了作为儒者的神圣世界。
朱子《家礼》【1】首创祠堂制度,涵括冠婚丧祭礼,是后世最简明适用的家庭仪则指南,是“儒家礼仪世俗化、平民化”的简明实用礼仪手册,在近世中国及东亚社会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朱子重视礼仪中心的建造,祠堂成为家礼践行的礼仪中心、神圣空间,是祖先灵魂神主的居所,是家庭居所的中心。《家礼》所有礼仪中,祠堂和祖先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家礼》将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礼仪,乃至日常洒扫应对,一一具列,显示其作为生活礼仪手册的特点,但是,除了“人事”,还有“天理”,除了“名分之守”还有“爱敬之实”,除了“修身齐家之道”还有“谨终追远之心”。这些人生礼仪的践行,除了实现现实人生之外的社会教化,朱熹还希望有超越的神圣的追求(有学者提出这是“宗教情怀”)。但这超越的神圣的面相,往往被大家所忽视。《家礼》建构的以祠堂为中心的“神圣空间”【2】以及宗教意涵,学界已有一些讨论。但祠堂本作为一个屋化/物化的空间,如何建构起神圣性,并成为一个神圣与日常交融的礼仪空间?这些问题仍有讨论的余地。本文希望在前贤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家礼》祠堂及其礼仪的的圣俗问题。
一、作为屋化空间的祠堂
朱子《家礼》最大的贡献是首创祠堂制度。《家礼》开篇就讲“祠堂”,以此“先立乎其大”,解释了祠堂设置的重要意义:“此章本合在《祭礼》篇。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后篇所有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然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家礼》卷一)可见,祠堂和祖先在家礼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祠堂体现的是“报本反始”“尊祖敬宗”的意义,其设立本身是为满足士庶大众祭祀祖先的需要,使其“施之有所”(《家礼·叙》)。
朱子重视祠堂空间的建构。首先,他在《家礼》卷一《通礼》首章就提出如何在家中创设祠堂,讲到祠堂设置之位置是“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祠堂之内“为四龛以奉先世之神主”,若遇水火盗贼,要“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器,然后及家财”(《家礼》卷一)。由于古来以东为上为尊,所以祠堂立于宫室正寝之东,从而确定了作为礼的空间的房屋要以祠堂为中心。对于家庙何以择址于此,朱子的解释是: “家庙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离外做庙。又在外时,妇女遇雨时难出入。”【3】可见,“神依人”,就是神追随至人的家居之中,祖先神灵参与到后世子孙的日常生活之中(后面将述及“祠堂中的人生礼仪”),这势必转换了祭祀的重点。
其次,《家礼》描述了作为屋化空间祠堂的外部形制。“祠堂之制三间。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令可容家众叙立。又为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于其东。缭以周垣,别为外门,常加扃闭。若家贫地狭,则止为一间,不立厨库,而东西壁下置立两柜,西藏遗书、衣物,东藏祭器亦可。正寝谓前堂也。地狭则于厅事之东亦可。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凡屋之制,不问何向背,但以前为南、后为北、左为东、右为西,后皆放此。”(《家礼》卷一)可见,按照朱子的祠堂规划,作为屋化的祠堂空间,应有三间,不仅能容纳四世先祖的神龛,而且还能有一个存放遗书、衣物和祭器的储藏室,以及一个为祖先神灵供奉食物的“神厨”。理想的情况,这个祠堂屋的前面还应该有一个“可容家众叙立”的“以屋覆之”的空间。此外,祠堂中门外还有两排阶梯,以便举行祭礼时以谨男女尊卑之名分、分别从东西台阶序列行进。
同时,朱熹也提到不必拘泥祠堂之大小,若家贫地狭,也可一间大小的屋子祭祖,以柜子代替厨库即可;甚至,地狭则以“厅事之东”为祠堂祭祖亦可。可见,《家礼》为解决贫窭者“终不能有以及于礼”的情况,确实在具体仪节、器物使用、场所设置等方面保持相当的弹性空间【4】。祠堂位于家庭空间之中,屋墙之内供奉着祖先的牌位,构成了一个家庭的生活秩序,以至于后世把祭祀祖先的祠堂选择出来作为中国家居的规定性特征【5】。特别是元明清时代,祠堂成为士庶住宅的一个普遍特征,房屋是以祭祖为中心的礼的空间。虽然朱熹主张祠堂放置在宫室之东侧,并非中心位置,但后世普遍放在中心位置,亦可见祠堂于家的重要意义。
再次,《家礼》对祠堂内部的陈设布局也描述得很仔细。朱熹继承前辈儒家学者提出的祭祀四世,祠堂之内“为四龛以奉先世之神主”【6】,“以 近北一架为四龛,每龛内置一卓。大宗及继高祖之小宗,则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神主皆藏于椟中,置于卓上,南向。龛外各垂小帘,帘外设香卓于堂中,置香炉香合于其上。两阶之间,又设香卓,亦如之”(《家礼》卷一)。可见,《家礼》祠堂内是奉祀高祖以下的四世之神主。在祭及始祖还是祭及高祖的问题上,北宋理学家张载、程颐等都有比较多的讨论,朱子的思想也历经几次变化,最后在“时宜”与礼经之间确定了比较符合礼意的“祭及高祖”。朱子按照这一思想在《家礼》中规划的祠堂制度,成为宋元明清宗法制度中一直沿用的宗庙制 度。【7】
正如有学者提到“中国将神的概念全部集中在祖先神上”,营造宫室首先建筑宗庙,“不仅是以示对祖先的崇敬,还因为宗庙的有无是判断能否担当都城的第一要 素”【8】。如 果没有宗庙,都城的神圣性以及合法性缺失,都城的功能亦无以成立。在家国同构的传统宗法社会,宋元明清以来宗族的功能则以祠堂这个屋化空间来承载。祠堂,是祖先神灵的居住地。这个屋化空间场所的设置,就是要建构一个家族的礼仪空间,让冠婚丧祭“施之有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朱子之后,祠堂成为民间家族祭祀的主要场所,这是《家礼》宗教性终极关怀的与众不同之处。《家礼》的最大贡献在于首创祠堂制度,建构了一个普遍的“神圣空 间”【9】。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屋化的空间,如何获得神圣性而成为“神圣空间”?
朱熹创制祠堂以祭祖,使家族祭祀礼仪的举行和对祖先情感的表达有一个物质依托,而且促进了宋明以来民间祠堂的发展,使其成为明清时期家族的象征,发挥了凝聚宗族的强大作用【10】。可 见,家礼之本,施于家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谨名分、崇爱敬”;于个人则修身齐家之道,与国家则“崇化导民”;同时,培养人的思想感情,“明乎其大”“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谨终追远之心”“不死其亲”,表达对祖先的怀念与感恩。而这一切“内外”的实现,都在祠堂这个空间之内完成。祠堂,这个屋化空间,既是一个和凡俗生活相接的礼仪空间,也是一个与祖先神灵人神相接的神圣空间。
二、祠堂中的人生礼仪
朱熹重视儒家生活礼仪的重建,他选择性地吸收了前辈的礼仪改革,编成《家礼》手册,为士庶人提供生活规范、日常礼仪之用,除讲解洒扫、应对等人伦日用之礼即通礼的一般原则外,还详细描述冠婚丧祭等日常生活之仪。朱熹早年“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深谙佛道教在世俗民间的影响之道,他致力于重振儒学,将士庶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环节诸如出生﹑成人礼、婚礼、丧葬以及祖先祭祀等行为规范都纳入儒学指导的范围,通过对世俗社会生活领域的再规范,希望不仅在思想领域也要在行为领域与佛道教争夺世俗社会的控制权。
朱熹倡导的儒家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家礼中的日常生活礼仪及冠婚丧祭礼,统一都在家里的祠堂里完成——犹如佛道信徒在寺院宫观的礼拜。祠堂,成为家礼举行的仪式空间,为儒家礼“学”真正转变为礼“教”提供了赖以依托的物化空间。而对于祠堂中的礼仪活动,何时在祠堂做什么,怎么做才是“行礼如仪”,《家礼》都给予明确的指导。
首先,规定相关日常生活礼仪在祠堂举行。《家礼》第一章突出了祠堂作为礼仪空间的中心地位,并确定在祠堂举行的日常礼仪:“主人晨谒于大门之内。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则参。俗节则献以时食。有事则告。”(《家礼》第一“通礼”)这些礼仪包括每天在祠堂的“晨谒”、一月两次的“参”和相关节日的正式供奉以及不定期的将家族内重大事项报于祖先。祠堂的礼仪空间里,主要参与者是“主人”即宗子。他每天早晨拜谒祖先灵位,焚香、鞠躬。主妇是主人举行仪式的襄礼者,和他的丈夫——主人一样,出入都要向祖先禀报请示。“主人主妇近出,则入大门瞻礼而行,归亦如之。经宿而归,则焚香再拜。远出经旬以上,则再拜焚香,告云某将适某所敢告,又再拜而行,归亦如之,但告云某今日归自某。”(《家礼》第一“通礼”)在新月和满月(即每月两次),新年和冬至日、夏至日,都要在祠堂举行全家参加的祭拜。全家人聚集在厅前,男人东面,女人西面,按照辈分站成排。主人负责举动男性祖先的牌位,主妇负责将女性祖先的牌位从龛中取出,把它们放在祭桌上享用供奉。主人主妇共同完成相关供奉。祠堂,成为活着的子孙与故去的祖先之间交流的空间,这里行礼如仪,在尊祖敬宗的同时,形成尊卑名分、爱敬有加的生活秩序。
在祠堂举行冠礼——男子的成人礼。“前期三日,主人告于祠堂”,接下来,在祠堂举行冠礼仪式,包括加冠、取“字”及宣告祝词等多个仪节。首先,“将冠者就席,为加冠巾”,祝辞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维祺,以介景福。”然后,为冠者“再加帽子。服皂衫,革带,系鞋”,祝辞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谨尔威仪,淑顺尔德。眉寿永年,享受遐福。”再次,为冠者“三加幞头。公服,革带,纳靴,执笏。”祝辞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耇无疆,受天之庆。”(《家礼》第二“冠礼”)礼成,“主人以冠者见于祠堂”(《家礼》第二“冠礼”),并向祖先告辞曰“某之子某,若某亲某之子某,今日冠毕,敢见”。在许多文化中,成年礼是一个社会性行为,而儒家冠礼却完全是家庭行为,至少是在家庭中完成的【11】,这实与儒家一贯的“成人之道”有关。朱熹引述司马光的话,解释了冠礼的意义:“所以责成人之礼,盖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行于其人,故其礼故其礼不可以不重也。”(《家礼》第一“冠礼”)
婚礼的一系列仪式中,祠堂也有着突出的中心位置,男女双方多次在祠堂向祖先禀告。婚礼采纳前,男方“主人具书,夙兴,奉以告于祠堂”,女方收书信后,“遂奉书以告于祠堂”;女方回信后与男方后,男方“主人复以告于祠堂”。迎亲前,男方“主人告于祠堂”,新郎到新娘家,“女家主人告于祠堂”。婚礼仪式结束的第三天(婚后三日),“主人以妇见于祠堂”。所谓婚姻者,乃“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家礼》第三“昏礼”),所以子孙后代的婚礼,需要报告祖先,以这样的告见方式,让那些已逝的祖先以魂灵栖居祠堂的方式参与到活人的生活世界。
丧礼是朱子《家礼》中最繁杂的部分,对丧礼仪节有很多细微的规定。朱熹一生多次遭遇亲人亡故之痛,屡行丧礼,与《家礼·丧礼》内容多所符合,但也有一些不同。【12】丧礼进行到后期需把亡人供奉于祠堂,“诣祠堂,奉神主出,置于座,还,奉新主入祠堂,置于座”。第二年忌日,“告迁于祠堂……毕,祝奉神主入于祠堂”。(《家礼》第四“丧礼”)
从以上可见,作为人生礼仪最重要的冠婚丧礼以及日常生活礼仪,祖先和祠堂均在其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祠堂,是祖先灵魂的居所,因为祭拜祖先,祠堂成为家礼的礼仪空间,也是节庆期间或家族有大事发生的聚集场所。虽然朱熹本人主观上并未将求福消灾与祖先崇拜联系起来,但在一般士庶心中,逝去的祖先仍会显灵,能够为子孙后代带来祸福,所以人们需要向先人汇报生活情况,供上祭品,并寻求指点。无论怎样,朱熹描绘了一个围绕祖先神灵而运转的家庭生活的仪式空间,它是整个住宅的中心,人生行仪的重要节点和重要事件都与祠堂以及祠堂的祖先链接。祖先以及祠堂,也在这样的仪式中一次次内化为家庭成员深层意识的存在。
三、祭之在祠——祠堂神圣空间的建构
祠堂既然是为了解决士庶人家祭祀礼仪而设立,祠堂的规制首先就是满足祭祀的需要。虽然祠堂不仅仅是举行祭祀活动的神圣空间,也是其他人生礼仪及相关家族活动的主要场所,但显然,日常生活礼仪及人生礼仪冠、婚、丧礼,与“祭之在祠”的祭礼仪式有着很大不同,前者只是报告祖先、见于祖先,并没有神人交接,没有享用食物。换言之,那个屋化的祠堂在前者告见于祖先的礼仪活动中,呈现的仍然只是一个凡俗的礼仪空间、公共空间,“祭之在祠”才赋予了祠堂祭祀空间的神圣性。
朱熹极其重视祭祀祖先,为把祭祀活动融入庶众的日常生活,朱熹不仅在文献及理论上深究,还实际践行,把有关祭祀的礼仪放在《家礼》第一条。宋以前,只有贵族之家才能设立家庙祭祀先祖,但是宋以后,所有士庶阶层都能在家设立祠堂祭祀祖先,实现了朱熹“施之有所”“祭之在祠”的愿景。《家礼》不仅制定了祠堂在房屋中的位置以及应有的规制,还规定了祭祀的次数和祭祀礼仪,形成一套完整、系统的祭祖仪式。《家礼》从祭祀对象、时间安排、空间布局以及具体操作过程,都有细致的描述,正是祭之在祠、祭之以时、祭之以物、祭之以诚,构建了祠堂空间的神圣性。
第一、祭之在祠。
祠堂,是专门的祭祀空间,是祖先神灵(神主)栖居的神圣空间,不同于日常生活空间。正是栖居在祠堂的先世神主,让祠堂获得了神圣性。诚如有学者指出的:“祠堂所塑造的神圣空间主要由祠堂及祠堂内部所供奉的祖先构成,先祖的神主揭示了一个绝对的基点,标明了一个中心。每一次礼仪活动均由祭祀开始,通过祭祀的程序唤醒常驻子孙心中的祖先之灵,祖先的降临使得祠堂变得神圣而庄严,神而明之的祖先威灵,或福佑万代、或惩戒不肖。祠堂这一安顿祖先之灵的空间也因而变成了神圣的,具有宗教性的空间。”【13】作为祖先亡灵象征的神主,其神圣性的获得在于神主象征了天地日月,“作主用栗,取法于时月日辰。趺方四寸,象岁之四时。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虽然后世制者因尺寸不周而多失其真,甚至用牌位充作神主,但“取象甚精”的祖先神位的象征意义,显然为屋化空间的祠堂确立了一个“绝对基点”,祠堂因此获得绝对的神圣性,一个凡俗的屋化空间也因此转化成了一个神圣空间。
第二、祭之在时。
祭礼和冠婚丧礼仪不同点之一,就在于祭礼不是一个一次性仪式,而是一年中要重复举行多次。《家礼》举行的祭祖时间,有四时仲月之祭(祭祀所有的祖先)、冬至之祭(祭祀始祖)、立春之祭(祭祀先祖)、秋季祭祢、忌日之祭以及三月清明之祭等。可见祭祖礼时间除了忌日之祭不明确外,其余祭祀都有确定的时间,其确定以遵循节气变化为据。《家礼》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秋季祭祢的时间确立,基本继承了程颐的理论——将祭祖仪式与自然界的生长变化、阴阳消长变化结合,如认为冬至为一阳之始、立春生物之始、季秋为成物之始,所谓因时而感,因时而祭,“像其类而祭之”(《家礼》第五“祭礼”)。朱熹晚年认为冬春始祖祭和先祖祭,因有僭越之嫌而不再举行。总体上,《家礼》对祭祖时间的设定范围广、考虑周全又突出重点,为后世祭祖礼仪提供了基本的时间框架。四季仲月、冬至、立春、季秋、三月上旬及忌日作为祭祀时间,因应不同季节,成为自然的“圣显”时间,所谓“祭之在时”也。
米尔恰·伊利亚德曾详细讨论过人类的神圣时间,他说:在某种程度而言,神圣时间是可逆的;通过一定的仪式,终止日常的时间序列,时间因此而具有一种可以称之为神显的新的维度,它的延续在本质上不仅具有一种特殊的节奏,而且具有各不相同的“使命”、相互矛盾的“动力”;时间的这种神显的维度可以通过自然的节律显示,重复;由于重复,因而也能够永远重复而变容、圣化、被人记住。【14】据此,可见《家礼》的祭祀时间其神圣的维度也是通过自然的节律显示,通过祭祀仪式,在可逆的时间中不断重复,祭祀的祖先也因此而“变容、圣化、被人记住”。
第三、祭必有物。
这是祭祀祖先的原则,也是后世子孙诚敬之心的外在而直接的体现。祭祖仪式中,祭品是子孙与祖先进行沟通的手段。祭祀中,通过奉献祭品,获得神人相接的机会,保证祖先灵魂降临歆享祭品,福佑后人。朱熹强调祭祀主诚敬,所以对于祭品的准备提出“随宜置办”原则。祭祀的“蔬果酒馔”大体有“果六品,蔬菜及脯各三品,肉、鱼、馒头、糕各一盘,羹饭各一碗,肝各一串,肉各二串”,并“务令精洁,未祭之前,勿令人先食及为猫犬虫鼠之污”(《家礼》第五“祭礼”)。
在《家礼》简化《仪礼》祭祀礼仪而成的十四个环节中,至少有九个环节是与祭品直接相关的,如“进馔”“三献”“侑食”“受胙”“馂”等。祭品是祭祀仪式中人神沟通的物质媒介,在仪式中的祭品,获得其神圣性。前面论及一般的日常礼仪及人生礼仪只是见、告于祖先,即使有祝辞,也不会有“尚飨”。但祭祀礼仪却不一样,在祠堂的神圣空间中,后世子孙和祖先以祭品作为中介进行人神沟通,祖先通过“尚飨”享用子孙的奉献的祭品,祖先则通过“受胙”“馂”的仪式赐福于子孙。
第四、祭之以诚。
《家礼》中反复申明“凡祭,主于尽爱敬之诚而已”(《家礼》第五“祭礼”)。在论及祭祀难于施行的问题,朱熹的回答一以贯之:“由何难行?但以诚敬为主,其他仪则随家丰约。如一羹一饭,皆可自尽其诚。”可见,朱熹对祭祀的要求,特别强调祭祀者以诚敬之心参与祭礼,通过外在的周旋升降的仪节程序,生发由内而外的祭礼的庄严、肃穆与神圣性。朱熹的礼学重视礼仪的践行与教化功能。但同时,他认为人的诚敬、神圣情感只有在仪式中才能得到充分表达。如涂尔干所言:“仪式是各种行为准则,它们规定了人们在神圣对象面前应该具有怎样的行为举止。”“仪式都具有神圣性,如果仪式不具有一定程度的神圣性,它就不可能存在”【15】。在这个意义上,朱熹比他的儒家前辈更乐意承认仪式中神圣事物的存在。
在祭祀的过程中,朱熹认为祭祀者不仅要外在仪节行为做到“周旋中礼”,还要在内心生起神圣感,即“诚敬感格”,如此,才能感格祖先神灵降临,与人同在。朱子曰:“盖神明不可见,惟是此心。尽其诚敬,专一在于所祭么神,便见得‘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则神之有无,皆在于此心之诚与不诚,不必求之恍惚之间也。”【16】
综上,在祠堂空间内,通过祭之在祠、祭之在时、祭之以物、祭之以诚的祭祀礼仪,祖先神灵在自然宇宙、血气相通的神圣感格下降临,与后世子孙同在。在时空、心物、人神感通中,共同构建了一个与祖先之灵共在同在的神圣世界。随着祭祀仪式的结束,这个神圣的空间又复归日常。如果说“祭乃教之本”,是《家礼》实践的社会功能以及外显的现实目的,那么“祭者,际也,人神相接”(《孝经·士章》邢昺疏),当是朱熹《家礼》通过祭礼实现神圣爱敬的超越追求。
四、结语:“祠堂”的意义世界
朱熹《家礼》对礼仪实践的贡献,较之于他的前辈,最大亦最具创造性的贡献就是将祖先和祠堂紧密结合。一方面,确立了儒学指导下士庶礼仪生活中敬拜的对象——祖先,这对于拥有无数神灵的前现代民间社会无疑是一件“革命性”的事件;另一方面,为一度飘摇的祖先神灵确立了一个永恒的居所——祠堂。作为礼学改革与实践家的朱熹,他竭力要为他的时代建立一个合适士庶日常生活的的仪礼体系,并真诚地希望重建一个在儒家指导下的圣凡合一的有序的生活世界。
祖先的神主牌位供奉在房屋中心的祠堂,祖先与后世子孙共享一个世界,故去的祖先一直与活人生活在一起,成为后世子孙生活的见证者,甚至参与者。同时祖先也以神灵的身份护佑着后世子孙,尽管《家礼》中朱子确实没有明确建议子孙向祖先求福禳灾,但祭祀仪式中“备膺五福,保族宜家”“惟时保佑,实赖神休”(《家礼》第五“祭礼”)的祝辞,无论如何,都是表达了子孙们向祖先真真切切的祈福与保佑。笔者赞同《中国祠堂》的作者对祠堂祖先的理解,他说:“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最独特的一点,是对远亲近属的祭祀,他们并没有把故去的亲人当成死者,而是当作能够显灵的神仙来祭祀。”【17】在与“祠堂祖先”共在的生活世界,祖先以一种活的积极的力量介入后世子孙的日常生活中。祖先的神灵寄身于祠堂的神主牌位之中,通过祭拜礼仪,血气感通,祖先与子孙同在。祖先护佑后世的子孙,活着的子孙则怀抱着感恩之心不断的追念祖先,那些“追怀报本”“恭伸追慕”“不胜感怆”“不胜永慕”(《家礼》第五“祭礼”)的祝辞无一不是尊祖敬宗的至诚表达。
诚然,就宗法制社会最根本的“世俗意义”而言,“祠堂的存在只是为了以祭祀高祖以下四代祖先的庙祭为媒介,力求加强小宗集团的团结”【18】。《家礼》在继承古代仪礼的同时,“以时为大”,作了相应的改革,如冠礼中就增加了祠堂告拜祖先的仪式,婚礼中又规定新妇三日参拜见告祠堂,所有冠、婚、丧人生礼仪以及家族的重要事项,都与祠堂祖先连接。通过这种礼仪安排与重构,祖先的权威与血亲观念得到加强,宗法制度与宗族观念重新建立起来,宗法的人伦关系和等级制度得到强调。
在世俗的意义世界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家礼》创制祠堂的“神圣意义”。祠堂因为祖先神主的存在,成为圣神与凡俗共融的空间,以祠堂为中心搭建了士庶人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又因为与祖先的链接,而有了儒者希望的意义世界。祠堂和祖先的存在,成为一个可以提升后世子孙生命意义的具体的空间场域。在祠堂举行的所有礼仪,不论是日常生活的人生礼仪还是专门祭祀祖先的神圣礼仪,所有的礼仪“基本上都朝向了崇拜祖先这一目标,成年和成家的义务都是为了侍奉祖先的灵魂”【19】。在这个意义上,祖先和祠堂,构成了中国人的“教堂”。血脉宗法之下,不忘其亲,不忘其所有生,在“成人”“成家”的路上,不断与祖先对话,开显儒礼下士庶生活的意义世界。
注释
1 本文引用的《家礼》为日本学者吾妻重二的《〈朱子家礼〉宋本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特此说明。
2 和溪在《礼俗流变中的神圣空间——朱子祠堂制度的建构》中提出了“神圣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交融”(《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3期),本文与之讨论的角度有所不同。
3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朱子全书》第 1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 3039 页。
4 周元侠:《朱子〈家礼〉的特质——基于社会教化的视角》,《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1期。
5 [美]白馥兰著,江湄、邓京力译:《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国中国的权力经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6 关于神主的形制、尺寸,可参考吾妻重二《朱熹〈家礼〉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9页。
7(5)吴飞:《祭及高祖——宋代理学家论士大夫庙制》,《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4期。
8 [日]佐川英治:《宗庙与禁苑——中国古代都城的神圣空间》,陈金华、孙英刚主编《神圣空间:中古宗教中的空间因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2页。
9 和溪:《朱子〈家礼〉的终极关怀》,《哲学动态》2020年第7期。
10 邵凤丽:《朱子〈家礼〉与传统社会民间祭祖礼仪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76页。
11 罗秉祥:《儒礼之宗教意涵——朱子〈家礼〉为中心》,《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2 粟品孝:《文本与行为:朱熹〈家礼〉及其家礼行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3 和溪:《礼俗流变中的神圣空间——朱子祠堂制度的建构》,《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3期。
14 [美]米尔恰.伊利亚德著,晏可佳、姚蓓琴译:《神圣的存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9页。
15 [法]爱弥儿·涂尔干著,渠敬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0、46页。
16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五,《朱子全书》第14册,第898页。
17 [德] 恩斯特·伯施曼著,贾金明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中国祠堂》,重庆出版社,2020年,第338页。
18 [日]井上彻著,钱杭译:《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99页。
19 [加]秦家懿著,曹剑波译:《朱熹的宗教思想》,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3页。
(作者来自西北大学哲学学院)
供稿: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