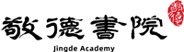礼学就是文化史之学
近年来,礼学研究整体上显示出复兴,乃至转盛的迹象,但尚存在不少问题。最近《古礼再研》《中国礼学研究概览》先后出版,这两部由武汉大学杨华教授著述和主编的新作与以往的礼学专论有所不同。
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可以说,礼是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礼学就是文化史之学。20世纪初,科举被废,礼学由显学沦为绝学,仅存一息,不绝若线。近年来,礼学研究整体上显示出复兴,乃至转盛的迹象,但尚存在不少问题:第一,各时段的研究有详有略,极不平衡;第二,关于“礼”的内涵外延理解各异,礼文化本身应有的研究内容不够完整;第三,没有处理好“礼”与“俗”的关系;第四,相较于微观研究,关于礼文化的理论问题思考不够充分。
最近,武汉大学杨华教授的新著《古礼再研》(以下简称《再研》)和他主编的《中国礼学研究概览》(以下简称《概览》)先后出版。两本著作贯通体用,概览古今,对以上问题做了较好的回答。
理论贯通是杨教授两本著作的显著特点。相较于其旧著《古礼新研》,《再研》的十九篇文章讨论的范围更广,时段更长,从先秦延伸至明清。其开篇《中国何以成为“礼仪之邦”?》,就考察了中国成为“礼仪之邦”的内在机制和历史过程。除了中国人对礼仪的自我文化认同之外,该文还梳理了域外视野中的中国礼仪。作者指出,正是在与西方礼仪的冲突中,中国传统礼仪愈加凸显,“礼仪之邦”的形象才得以固定和强化。《“礼崩乐坏”新论——兼论中国礼乐传统的连续性》则指出,从先秦至明清,历代都存在所谓“礼崩乐坏”的说法,这是儒家学说中的一个基本话语,也是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的常见感叹。每立新朝,则又开始制礼作乐,反映了历代统治者对于中国礼乐传统连续性的维护,是中华礼乐文脉得以延续和传承的文化基础。
在这两本著作中,其研究题目涉及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段。最早的一篇讨论了叶家山西周早期墓葬,关于秦汉时期则讨论了秦简法律问题和帝国的神权统一问题,涉及中古时期的则有庆氏礼学传承问题、汉唐孝道问题和唐代《开元礼》问题,涉及宋代的则有家礼问题和朱熹制礼问题,涉及明清的则讨论了酬世文献问题,涉及晚清的则讨论了理雅各《礼记》翻译问题。对以上问题,他都用自己的眼光予以整体研究,将各个时段的礼学问题视为连续而未中断的文化史现象。
《概览》也是如此,全书共分十一章,除了礼学通史和通论,还分别介绍了先秦至晚清民国时期各时段的礼学研究概况。由于相关研究在各个时段存在着失衡和割裂,因此《概览》在篇章结构上注重缀续古今,分段并重。对于研究较为薄弱的时段,如三国两晋南北朝、辽夏金元、晚清民国,在第三、五、六、九章专门加以概览评述,使礼学研究的介绍有所连续。该书第十、十一章为日本和西方汉学界的礼学研究介绍,对于从业者大有裨益。英文学界特别重视理论思考,例如关于“礼仪空间”的讨论,就反映了西方人类学和宗教学领域的理论传统,殊为难得。
杨教授特别强调广义的礼学研究,即接近于文化史范畴的“大礼学”。一般认为,礼学就是“三礼”文献之学。他认为,礼学应当包括礼典、礼义、礼论、礼俗、礼法、礼乐、礼教等多个侧面。在现代人文学的体系中,这些内容分属于文献学、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法学等多个学科。不少学者都指出,应当进行跨学科的礼学研究,但长期的学科壁垒,使其言易而行难。例如,《再研》中收录了两篇关于乡饮酒礼的文章,即《僎的“复古”与乡饮酒礼流变》和《朱熹与宋代的乡饮酒礼变革——兼论礼制对宋代地方官僚政治的回应》。但它们不是常见的朱熹礼学文献研究或朱熹礼学思想研究,而试图通过乡饮酒礼仪式的变迁,揭示礼学史波浪式流变的规律,又通过宋代的礼制设计来观察当时官僚制度的人事变革,把礼学史与制度史融合起来。他通过对理雅各英译《礼记》的研究,认为理氏的翻译局限于他在清代所见到的一般性科举文本,而未采用当时水平最高的研究文献;理氏传教士的身份所导致的文化差异和基督教视角,使其翻译并不能完全达意。这已经突破了一般翻译史和国际汉学的视野,将礼学、文献学、翻译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熔于一炉,研究起来绝非易事。
杨教授的研究十分注意新材料,其《再研》中有两类材料引人注目。一是出土文献。他利用青铜铭文和考古实物,指出叶家山曾侯墓葬中的丰碑、毁兵、族墓和都城、族徽、助丧等礼仪,都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仪礼》等文献可以对证,显示出商周时期南北各地的礼制共性。《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第25-28号补说》一文,则指出秦朝《祠令》的存在,后来公布的岳麓秦简印证并丰富了他的相关认识。《“大行”与“行器”——关于上古丧葬礼制的一个新考察》一文,结合楚简材料和商周青铜铭文,证明传世文献中的“行”和“大行”都与丧礼有关,是死亡的讳称,青铜“行器”也可视为随葬的“遣器”,从而修正了历代文献中的误解。《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出土简帛与〈封禅书〉〈郊祀志〉的对比考察》,则利用简帛材料,分析了从秦皇汉武到西汉末年的神权统一进程,认为秦汉帝国的国家祭祀重心不断向东向南转移,这与秦、楚、晋、齐等祭祀圈被逐渐整合成为国家“大一统”祭祀体系,几乎处于同步的历史进程。
二是酬世文献。《再研》中的《〈酬世锦囊〉与民间日用礼书》一文,以《酬世锦囊》等为线索,考察“民间日用礼书”的出现原因、编纂体例等,将其流行归因于清代社会广泛的礼仪需求和重视日用应酬的礼学文化。有学者评价此文“开启了中国近世民间社会以‘日用应酬’为突出特点的礼仪文化研究的端绪”(《楚学论丛》第十辑,湖北人民出版社,第394页)。这些都反映了作者对新出材料的重视。
作者还非常重视打通“礼”与“俗”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家礼撰作及其当代价值》认为,宋代以来家礼的制作正是由礼入俗的表现,推动了中国古代礼制“下移”的进程。在《概览》中叙述每个时代的礼学研究时,都设有礼俗的专节、专目,以考察当时的日常生活和民间信仰。作者认为,历代平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时令节庆、器用杂物,莫不透露着礼制的痕迹。
诚然,作者的研究还存在不少有待完善之处,比如关于礼学的外延界定问题,关于某些考证的细节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讨论。但总体而言,《再研》和《概览》反映了作者的学术追求。一是明确的问题意识,即所有选题都试图回应“中国何以成为礼仪之邦”这一问题;二是广义的礼学研究对象,即奉行钱玄先生所谓“三礼之学,实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学”,将礼义、礼典、礼法、礼仪、礼教、礼俗等问题综汇起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三是时代贯通的研究范围,即不限于某一时段,而将从上古到晚清的礼学问题都纳入自己的学术视野;四是新鲜的礼学材料,即在传世文献之外,将金文、简帛等出土文献和晚近酬世类民间文献都纳入礼学研究的范畴。
由是,这两部新著与以往的礼学专论有所不同,值得向读者推荐。
(作者:景灿涛,单位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供稿: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