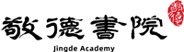孟子的人性论:铜铁时代转换与人禽关系翻转的产物
时间:2022-08-13
浏览:164
人性论是关于人类特性与本质问题的理论,是人类的自我意识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人是一种类存在物。所谓人性,是指人类作为大千世界的存在物之一,与其他类存在物相比,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孟子的人性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性,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一是社会性,就是“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章句下》第十九章)
几希,微不足道也。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极其微小的。然而,就是这极其微小的区别所在,决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即“人性”。那个时候的人,自然不懂得人是从动物界演变过来的,但从对人与动物的行为特征的观察和比较中,不难发现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很多时候,人与动物的行为方式简直差不多,人兽界限是模糊的。孟子的人性论,就是使这模糊的界限鲜明起来,以区别“人”与“非人”(以禽兽为代表)。他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章句上》第六章)

孟子画像
“几希”是什么?就是指“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无法忍受别人受苦遭难之心也,即恻隐之心,也就是同情心。恻隐之心是仁的发端,在上述“四心”“四端”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孟子有时直接以“仁”规定人,如说“仁也者,人也”(《尽心章句下》第十六章);或规定人心,如说“仁,人心也”(《告子章句上》第十一章)。很多时候只说“仁”,等同于说仁义或仁义礼智。严格说来,人性并不是指仁、义、礼、智(所谓“四德”),而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或“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所谓“四心”)。后者分别是前者之“端”。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章句上》第二十一章),把这个意思说得很清楚了。“根于心”,所以是“端”。既然是“端”,就已经是仁、义、礼、智了,孟子也直接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章句上》第六章)。但从定义上说,是大不相同的。因为只是“根”只是“端”,所以才是“几希”的,也才是不容易保存的,只有君子才做得到,而且“存心”不易,常常变为“放心”(存而复失)。几希,虽然从数量上看极其微小,从界限上看模糊不清,但就是这一微小、模糊的区分,把“人”和“非人”区别开来:不但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更重要的是,把人自身内在的“人性”和“兽性”区别开来。人身上的“兽性”或者说“动物性”是什么?就是“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人与生俱来的感官欲望或爱好或本能,与禽兽是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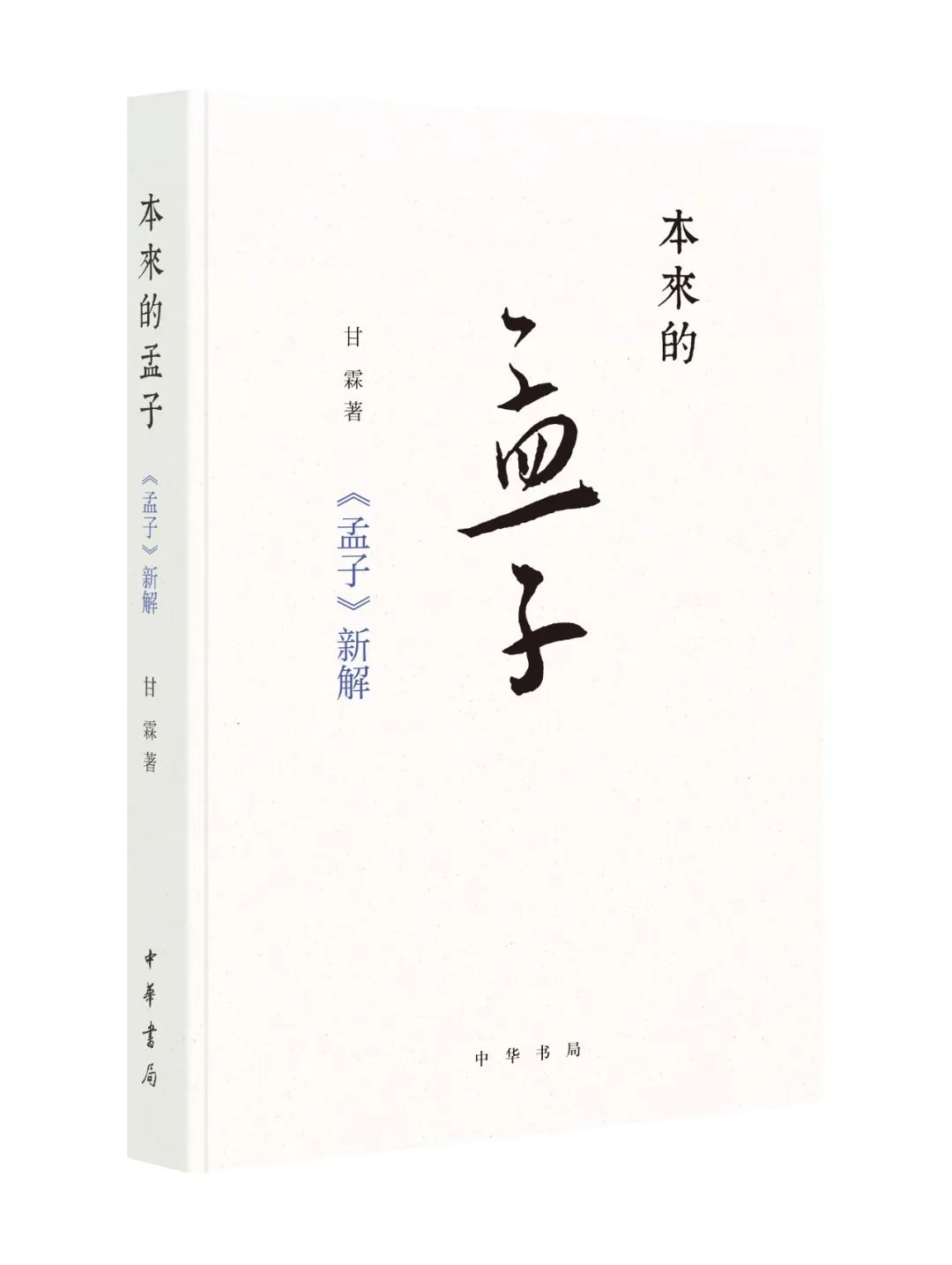
认为人是集“人性”与“兽性”(孟子就叫“禽兽”)于一身的存在物,人的“人性”部分才叫“人性”(孟子常常叫作“性”),人的“兽性”部分不属于“人性”,也不能叫做“人性”,是孟子人性论的独特之处。他反对告子“生之谓性”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告子把人身上的“人性”和“兽性”混为一谈了。比如告子所说的“食、色性也”,孟子认为不成立,食、色只是人与动物相同的本能而已,不属于“人性”。当时人及后世之人,在人性问题上,绝大多数持有的是告子的观点。今天的人,对于孟子的“人性”概念,除了不免于与告子的观点混淆之外,还容易出现的一个误区,是将“自然性”与“社会性”的概念套用其上,将“兽性”等同于自然性、“人性”等同于社会性。实则既然叫“人性”,性即生,与生俱来,就只能是自然性。如果用进化论的思维解释,可以这样描述:在人类生命自然演化史上,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人类的动物祖先处在孟子所说的“禽兽”阶段,只具备纯粹的“兽性”即动物性;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人类的动物祖先开始有了孟子所说的“人性”,“它”开始变成“他”,即开始成为“人”,但人的“兽性”仍在。不妨说,人是具有“兽性”的人,是具有“人性”的兽。人类仍在进化,但显然不能说人身上的“人性”与“兽性”是此长彼消的,只有人的社会性即文化可以起发挥“人性”而抑制“兽性”的作用。描述只能到此为止了,在孟子看来,人的“人性”是“分定”(分量确定不易)了的,所以环境、条件等后天的各种因素,无论好坏,影响的只是后天行为“为善”还是“为不善”,并不能影响“人性”的一分一毫:“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尽心章句上》第二十一章)

孟子的“人性”定义,是伦理学的,也是认识论的。部分是伦理学的,因为是可论证的,他举出的“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的例子就是。部分是认识论的,因为有一个如何定义的问题,孟子的逻辑是将人的自然性截然分为“人性”与“兽性”,他的论证是根据这种定义而进行归类。在伦理学的意义上说,孟子的逻辑是混乱的(被荀子批评为“无类”);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说,孟子的论证是强词夺理的(时人目之为“好辩”)。但是,在伦理学和认识论结合的意义上,即在人的社会性或文化的意义上说,孟子的论证是经验的,逻辑是先验的。孟子的人性论,未尝不是一种强有力的学说。以上说的是孟子人性论的一个方面: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接下来说说另一个方面:人之所以异于人者,孟子叫“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人”,是指人类,即所有人、每个人。“分定”,是说所有人的“人性”都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理想社会也就很容易实现:仁、义、礼、智之“端”既然是每个人天生具备的,“思则得之”,每个人又都可以设身处地、力所能及地去做。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告子章句下》第二章)对治人者来说,治理天下不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梁惠王章句上》第七章)但是,社会的实际情况是等级分明、阶级分明、千差万别的,这个应该怎么看待?孟子的解释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即“人性”,在人出生的时候是一样的,很小的时候也几乎一样(他用孺子或赤子的行为论证“人性”的存在),以后则分化了:一部分人成为“君子”,一部分人成为庶民或“小人”,这是因为前者对“人性”存之,后者对“人性”去之。为了说明上述问题,孟子发明了“大体”“小体”的独特概念:“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从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小者为小人。”所谓“大体”,指心。所谓“小体”,指耳、目、鼻、口和四肢。他认为,被心这个思维器官所指引的人是“大人”,被耳、目、鼻、口、四肢这些感觉器官所主导的是“小人”(《告子章句上》第十四、十五章)。社会的等级、阶级由此产生:大人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章句上》第四章)社会矛盾百出,是因为君子、大人即劳心者,他们并不总是“从其大体”,也并不总是“存心”,而常常出现“从其小体”,动不动就“放心”(即丧失“本心”)的情况。君子、大人的修为,就在时时都要“存其心,养其性”,以不失去其“本心”,一旦失去,又时时都要寻找回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章句上》第十一章)

孟子的人性论,基于人禽之辨。人禽之辨,是人类作为认识和实践的主体,从从属于自然界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将自然界对象化的过程。孟子所揭橥的战国时期的人禽之辨,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次大觉醒,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一次大进步。其所以发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铁器时代的到来,促使青铜时代的主导性思想文化发生转折性变化。中国的青铜时代,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夏代初期,至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战国晚期才告结束,为铁器时代所取代。积年共1800余年,与夏、商、周三代相始终。在漫长的青铜时代,一个突出的现象,如张光直所说:“金属始终不是制造生产工具的主要原料;这时代的生产工具仍旧是由石、木、角、骨等原料制造。”(《中国青铜时代》第12页)当时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青铜便集中用于制造礼器和兵器,而尤以礼器为大宗,服从并服务于获取政治权力并维护政治秩序的需要。按照张先生的观点,青铜器是统治者通天的工具,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是通达天地的助手。在殷商和西周的铜器纹样中,最常见的动物母题为饕餮纹,饕餮面形常常构成一个铜器全部装饰花纹的中心,表现出神秘和奇异的色彩;若干铜器的组合,呈现威厉、森严的气氛。可印证的是,在同时期的神话中,动物往往具有神性,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玄鸟即燕子,商族的始祖诞生和燕子有关;又如周族始祖后稷出生后被弃,“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诗经·大雅·生民》),牛、羊、鸟为后稷的保护神。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神奇的动物具有很大的支配性的神力,而对动物而言,人的地位是被动与隶属性的”(同前书第417页)。

商代的饕餮纹鬲
东周时代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从春秋中叶至战国中叶,是剧烈变化的阶段。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包括饕餮纹在内,已经形式化了,不再具有神异性或神异性大大减弱。在同时期的神话中,人与动物的关系也转变了,“人从动物的神话力量之下解脱出来,常常以挑战的姿态出现,有时甚至成为胜利的一方”(同上页)。孟子也曾描述这种情景:“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定所,……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滕文公章句下》第九章)鸟兽害人,禹驱蛇龙,人得安居,代表了一种崭新的时代景观。在孟子的这个叙事里,尧和禹还多少留下神、人兼备的痕迹。在其他多数的叙事里,尧和禹只是人间的圣王。而他们之为圣王或圣人,实际上是神话历史化的结果。上述人与动物关系的转折性演变,与人工制铁的出现以及铁器的普及化进程,大体上是同步的。人工制铁出现于在公元前9世纪的西周晚期,春秋时期有了初步的发展,至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春秋战国之际开始进入迅速发展阶段。与青铜器发展性质上不同的是,铁器以生产工具、兵器和日用器具、车马机具等实用类型为主(参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第二、三、四章)。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铁制农具的利用有所普及。“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的“耒耜”,应该不再是木制,而是铁制,因为孟子在与陈相的对话中,提到了“釜”(铁锅),特别是“以铁耕”,用“铁”来代指某种铁制耕田工具,而且“以粟易之”,已经有了铁器贸易(《滕文公章句上》第四章)。铁制农具在当时应该还是比较值钱的,所以有“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的说法(《滕文公章句下》第三章)。毫无疑义,铁器时代的到来,特别是铁制生产工具日益广泛的利用,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增强了人在自然面前的自我意识(区别于自然)、主动意识(挑战和征服自然)、主体意识(认识自然)。人禽之辨,实质是人禽关系的翻转,人的地位大大上升。孟子的人性论,是基于人禽之辨而对于人的特性和本质的深度思考。而他的其他思想主张,则是人性论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以及天下层面的逻辑延伸。